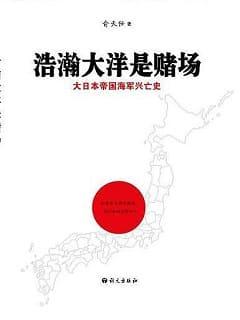- [ 免費 ] 引言
- [ 免費 ] 第壹章 來了些洋船黑乎乎 ...
- [ 免費 ] 第二章 東亞現代史從朝鮮開始 ...
- [ 免費 ] 第三章 “最討厭的就是丁汝昌 ...
- [ 免費 ] 第四章 機會來了
- [ 免費 ] 第五章 制海權的問題
- [ 免費 ] 第六章 誰開了第壹炮? ...
- [ 免費 ] 第七章 啊,大東溝
- [ 免費 ] 第八章 龍旗在黃海上最後壹次 ...
- [ 免費 ] 第九章 和老毛子也來壹把? ...
- [ 免費 ] 第十章 老天爺餓不死瞎家雀 ...
- [ 免費 ] 第十壹章 再出老千,確保制海 ...
- [ 免費 ] 第十二章 “浦鹽艦隊” ...
- [ 免費 ] 第十三章 瘋狗艦隊往東來 ...
- [ 免費 ] 第十四章 船往對馬來? ...
- [ 免費 ] 第十五章 對馬
- [ 免費 ] 第十六章 回頭檢討,運氣真好 ...
- [ 免費 ] 第十七章 長蛋壹扯三十年 ...
- [ 免費 ] 第十八章 八八艦隊好難搞 ...
- [ 免費 ] 第十九章 風向軍國吹
- [ 免費 ] 第二十章 昭和海軍三大事件 ...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空軍不是光靠飛出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 “三駕馬車”的神 ...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 為什麽要贊成三國 ...
- [ 免費 ] 第二十四章 再賭壹把珍珠港 ...
- [ 免費 ] 第二十五章 最後的天佑 ...
- [ 免費 ] 第二十六章 大英帝國雕落了 ...
- [ 免費 ] 第二十七章 中途島真的僅僅是 ...
- [ 免費 ] 第二十八章 怎麽會有“命運的 ...
- [ 免費 ] 第二十九章 其實海權的決定並 ...
- [ 免費 ] 第三十章 挨餓的原因是什麽? ...
- [ 免費 ] 第三十壹章 來了新靈感,日美 ...
- [ 免費 ] 第三十二章 大姑娘上轎,皇軍 ...
- [ 免費 ] 第三十三章 瓜島無窮盡,山本 ...
- [ 免費 ] 第三十四章 新長官的作戰是“ ...
- [ 免費 ] 第三十五章 鬼畜把皇軍打成了 ...
- [ 免費 ] 第三十六章 這次是真的反攻了 ...
- [ 免費 ] 第三十七章 發現長官不見鳥 ...
- [ 免費 ] 第三十八章 豐田副武被當上了 ...
- [ 免費 ] 第三十九章 帝國海軍航空兵在 ...
- [ 免費 ] 第四十章 要想活,殺了東條再 ...
- [ 免費 ] 第四十壹章 重要的是要加大改 ...
- [ 免費 ] 第四十二章 來將是牛還是狗? ...
- [ 免費 ] 第四十三章 莫把信息當情報 ...
- [ 免費 ] 第四十四章 可以“國破山河在 ...
- [ 免費 ] 第四十五章 使了個大勁,放了 ...
- [ 免費 ] 第四十六章 最後的日本海軍提 ...
- [ 免費 ] 第四十七章 能幹的就只有神風 ...
- [ 免費 ] 第四十八章 菊花雕零在太平洋 ...
- [ 免費 ] 第四十九章 沒了骰子,只能歇 ...
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三章 “最討厭的就是丁汝昌”
2018-9-28 21:29
1891年7月13日,離甲午戰爭還有四年。
東京小石川炮兵工廠的小石川後樂園。受外務大臣榎本武揚的委托,海軍大臣樺山資紀中將在這裏召開壹個遊園會形式的歡迎宴會。貴賓是大清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和正在日本訪問的包括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鎮遠號”在內的七艘軍艦上的50名大清水師軍官。
樺山資紀氣惱地對海軍次官伊藤雋吉少將說:“最討厭的就是這個丁汝昌,榎本外相硬要講什麽‘日清友好’,這樣,明天全體出動去會會這個遲早要在戰場上見面的敵人,大家都把這個丁汝昌的臉給我記住了,把軍務局長喊來。”
當時的海軍省軍務局長就是伊東佑亨少將。伊東壹進門,樺山資紀就問了他壹個問題:“伊東君,妳說丁汝昌這次為什麽走這麽條怪路,從下關進日經瀨戶內海繞紀伊半島到東京來?”
這位後來指揮著聯合艦隊大敗北洋水師,壹直晉升到元帥海軍大將的伊東少將回答說:“丁汝昌這是在向我們示威,那意思是說日本的內海就是北洋水師的庭院,如果日清開戰,他能指揮著北洋水師壹口氣攻到東京。去參加歡迎宴會沒問題,但請大臣無論如何也要懇請外務大臣和首相同意我們也去訪問壹次清國”第二天,伊東佑亨在遊園會上劈頭對丁汝昌就說:“丁提督,能不能讓我參觀壹下妳們偉大的超級戰艦‘定遠號’?”
丁汝昌坦然地笑了笑:“什麽時候都非常歡迎,但是您只能看,我們不會回答您提出的問題。”
丁汝昌有資格坦然,這艘長達95米,滿載排水量7355噸,航速16節的德國造戰艦“定遠號”是當時遠東的最大新型戰艦,裝備在“定遠號”上的兩門30.5厘米雙連炮能夠毫不容情地把所有敵艦送進海底。讓妳伊東佑亨參觀壹下又怎麽樣?
第二天伊東少將在丁汝昌的陪同下參觀了“定遠”“鎮遠”兩艦。
樺山海軍大臣在海軍省等著伊東的報告。
而伊東的報告是:“如果現在和清國開戰,我們沒有勝利的可能,只要‘定遠’和‘鎮遠’兩艦就能把全部常備艦隊送到海底。閣下,軍艦,我們要軍艦,我們是四面環海的海國,衛國就是衛海,擁有能和‘定遠’對抗的軍艦是我們最要緊的。”
樺山嘆了壹口氣:“李鴻章的目的達到了”被稱為海軍的“頭腦”位居軍務局長,實際上指揮著日本海軍的伊東佑亨被逼著說出來了“沒有勝利的可能”李鴻章派丁汝昌率北洋水師訪日的目的——向日本示威的目的,確確實實地達到了。
其實,在這之前5年,1886年的8月,北洋水師就派出以“定遠”“鎮遠”兩艘主力巡洋艦為首的四艘軍艦(還有兩艘是“濟遠”和“威遠”訪問過日本,帶隊的還是丁汝昌,那次是在黃海演習完畢以後,開到長崎去修理軍艦去的。修理軍艦也沒有必要到日本去,所以其實有個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裏面。但那次的長崎寄港鬧出了壹個在日本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的“清國長崎水兵事件”北洋水師士兵因為嫖妓和日本警察發生沖突,雙方大打出手,死10人,傷70余人,結果是日本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了事)。
時隔五年,北洋水師雖然沒有增加新艦新炮,但還是讓伊東佑亨垂頭喪氣。
但有人不這麽看。
回航時北洋水師還是走瀨戶內海,在廣島的宮島錨泊時,接受了吳鎮守府長官中牟田倉之助中將和參謀長東鄉平八郎大佐的訪問。在這次訪問“平遠號”聲稱故障,進入吳軍港檢修,其實是有點觀察和偵查日本海軍技術程度的意思。
但是結果是北洋水師的底細被人家摸了個底掉。
東鄉平八郎大佐幾乎每天不是軍服就是便服在碼頭觀察“平遠號”最後的結論是:“清國艦隊不足為慮,他們只是壹把褪了火的寶刀。寶刀確實是寶刀,但是已經褪了火,真正需要的時候派不上用場”為什麽這麽說呢?用東鄉的原話:“神聖的炮口上,掛了不少東西,從內褲到襪子什麽都有,怎麽看怎麽像晾衣桿,這還是在外國的港口呢,甲板上也是亂七八糟,根本就沒有整理”“炮口是軍艦的靈魂,從清國艦隊能夠毫無顧慮地這樣做就知道這支艦隊的士氣,從軍官到士兵沒有任何緊張感,軍艦本來所具有的力量發揮不了,沒什麽可怕的”這是在說海軍的軟件,沒有配套的軟件,光有硬件是不能被稱為海軍的。
東鄉平八郎看出了北洋水師是軟件配套沒有趕上硬件購置。
但日本海軍呢?在這方面不得不承認日本海軍的建設是先從軟件建設開始的。
19世紀後半期的日本是壹個落後的農業國,為什麽能像變戲法壹樣出現了壹支包括陸海軍的很強大的軍隊?應該歸功於日本的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兵學校這兩個培養軍事指揮官的軍事院校的辦校成功。
明治二年(1869年)兵部省在《應該創立大海軍的建議》中是這麽說的:“軍艦因為士官才有精神,沒有士官,則水夫將無所作為。水夫無所作為,則艦船也就成無用的廢物。而海軍士官所必須掌握的深奧學術的練成絕非容易之事,所以當前壹大緊要事項就是盡快創辦學校。”
建設壹支海軍,需要的東西很多,比如起碼要有軍艦,要有操縱軍艦的人員和這些人員如何構成的組織。壹般來說這三要素裏最引人註目的就是軍艦,但其實軍艦問題其實最好辦,最簡單。只要拿得出錢,什麽都能買的到。當時英國,法國,德國,俄國還有美國全都在亞洲膘著勁明爭暗鬥,什麽最新式的軍艦都買得到,困難其實是人員培養訓練和編成控制。
在伊東佑亨大發沒有軍艦的感嘆時,日本海軍已經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來努力培養和組織海軍人材了,而且這種努力的效果已經到了初見成效的時候。
1870年,明治政府模仿幕府的“長崎海軍教習所”在東京的築地開設了“海軍操練所”第二年改名為“海軍兵學寮”到1876年改名為“海軍兵學校”1888年搬到了廣島縣的江田島,在東京的海軍兵學校原址上辦了海軍大學校。中國人通常把在江田島的海軍兵學校稱為“江田島海軍學校”這要歸功於林立果在《五七壹工程紀要》裏使用了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電影《啊,海軍》裏面的翻譯。
海軍兵學寮和陸軍士官學校的前身“兵學寮”同時設立,可改名字比陸軍晚了兩年,這麽壹來“士官”這個詞被陸軍用了去,只好湊合著用“兵學”這個學究氣十足的詞了。其實陸軍有點怪,在除了“陸軍士官學校”這個校名之外再也不用這個詞,用的是“將校”可是海軍除了學校名不用“士官”這個詞以外在其他場合則是大量使用這個詞。
在日本海軍術語中,“士官”不是指的“下士官”而是相對於“士兵”而言的反義詞,也就是“軍官”的意思。少尉是“士官”大將也是“士官”日本陸軍1887年開始從法國式轉為普魯士式教育。海軍的轉型更早,從海軍操練所設立開始就從原來的法國式教育轉到了英國式。1873年開始英國派出以後來壹直做到北美艦隊上將司令官的道格拉斯(Douglas,Sir ArchibaldLucius)少校為首的34名教官來日本,英國人在日本壹呆就是17年,合計69人次,道格拉斯本人就在日本呆了兩年,如果不是有人警告他如果再趕緊不回國可能會影響到晉升的話,可能還會繼續逗留下去。
海軍兵學校和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英國達特茅斯皇家海軍學院壹起同列被譽為世界三大海軍學校,因為曾幾何時這是三大海軍強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仔細想壹下還是有點不可思議,和精神要素占得更多的陸軍相比,海軍更加受到國力的制約,這個海軍兵學校既然是海軍的壹部分就也應該不例外。貧窮的日本是如何辦出這個海軍兵學校的?
當時的日本是壹個很窮的落後小國,培養海軍人才最簡單而又便宜的方法應該是送人去歐美留學。其實在壹開始日本人也是那麽想的,比如東鄉平八郎就被送去英國留學,還壹去就是八年。
但是有壹點弄不明白的事情是:日本的海軍留學生到處被人拒絕,是看不起這些黃皮猴子還是為了保守海軍機密沒人知道,反正就是到哪兒哪兒不要。
像東鄉平八郎想去英國進達特茅斯皇家海軍學院,結果到了那兒別人才對他說不行,結果只能上商船學校。
沒辦法才只好從壹開始就自己辦學校,而且還是斥巨資全部請英國人來幫忙。當然英國是當時第壹海軍大國是日本人為什麽請英國人的最主要原因,更加直接的原因就是在1863年的薩英戰爭中知道了英國海軍的厲害。
1862年在現在的橫濱市生麥地方發生了所謂“生麥事件”四個英國人騎馬沖撞了薩摩藩主島津久光的行列。其實就在事情發生前幾分鐘,美國領事館官員範李德也遇到了這個行列,按照歐洲人見了貴族或婦女的馬車要下馬讓路的禮貌,範李德讓了路,沒有出事。但這幾個英國人在中國上海呆過很長時間,騎在馬上鞭打黃種人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大鼻子怎麽能給黃皮膚的日本人讓路?於是和藩主的武士發生了沖突,壹個叫理查遜的英國人被日本人把腸子砍出來了,拖著腸子想逃跑,另壹位武士“看到他很痛苦,就幫他做了介錯”壹刀把理查遜的腦袋砍下來了。兩個重傷,剩下壹個是個女的,叫波羅黛兒,倒是沒受傷,但給嚇瘋了,不久也死了。
約翰牛們很吃驚,這是他們第壹次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大英帝國的臣民也是可以被人砍殺的,而且是黃種人。於是就去找幕府論理,要幕府賠錢10萬英鎊。幕府給來了個壹問三不知:那是薩摩藩,妳得找他們。於是英國人就出動了10艘軍艦上鹿兒島來討說法來了。
英國人到了鹿兒島,看看這麽個鄉下地方,料想也拿不出10萬英鎊,就減到了二萬五,但要處分肇事者。遇到翻譯又差勁,把“肇事者”給翻成了日語的“責任者”藩主島津久光壹看急了眼:八格丫魯,要處分老爺?老爺跟妳拼了吧。這就打了起來,壹仗打下來,全日本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薩摩藩取得的壹點成果全部毀於英軍炮火,但死人不多,才五人。而反過來看來勢洶洶的英國人卻死傷63人,包括旗艦尤裏亞勒斯(HMS Euryalus)艦長約瑟林副艦長魏爾默全去見了上帝。
怎麽會打出這麽個怪結果來?其實那天可能上帝沒玩過天照大神,對英國人有點不公平。首先炮戰剛開始時海上風浪大作,英國軍艦顛簸得厲害,無法瞄準,對薩摩藩的海岸炮臺無法造成損傷。而英國艦隊停泊的地方又正好是薩摩藩炮臺平時訓練時停靶船的,這樣薩摩炮臺練瞄準都省了,壹炮打出去就直接命中英軍旗艦。
但隨著天氣變好,英國軍艦上配備的最新式阿姆斯特朗炮的威力就顯示出來了。薩摩藩的海岸炮臺被敲了個精光不說,剛剛建成的造船廠和其他近代工業全完了蛋,這才兩家人坐下來談判。
後來薩摩藩還是賠了兩萬五千英鎊,但不是薩摩藩自己的錢,向幕府借了六萬三千兩銀子賠了英國人以後就沒還,賴掉了那筆帳。
大山嚴,黑田清隆,東鄉平八郎全是參加過那場戰爭的,因此大家全同意要辦海軍,除了向英國學習外沒有別的出路這種說法。
日本人在薩英戰爭中看著英國人耍酷,眼饞得口水支流還不光是軍艦大炮和海軍。日本人發現英國人打仗時甲板上有軍樂隊在奏樂,認為非常地妙。這邊談判還沒有探出結果,那邊就有人爬到英國軍艦上要人家教他們玩洋鼓洋號,回來自己就練了起來,後來日本海軍的大型艦只上壹直有軍樂隊的編制,平時在艦上練練樂器兼管打掃衛生,戰時運運炮彈兼管吹吹打打,由來就是從薩英戰爭裏跟英國人學的。
日本人辦這個學校是很認真的,認真到了什麽程度呢?連為什麽海軍兵學校會搬到廣島的江田島區都能夠說明問題。隨著經濟的逐步繁榮,海軍省認為學校辦在繁華的東京會引起學生們思想墮落,所以才找了這個當時是鳥都不來做巢的廣島荒島,遷校之前還和當地豪紳簽訂了壹個名為《江田島取締方始末書》的合同,裏面規定在江田島指定範圍內不得有“猥藝醜行”就是說不能開娼館妓院,以保持教育環境。而壹直到1945年日本敗戰為止的57年間江田島還確實是做到了這壹點。至於到後來設施被美軍接收,飛燕流鶯從全日本和全世界各地雲集江田島,繁榮娼盛則是以後的事情了。
和所有海軍名校壹樣,江田島海軍兵學校最豪華的建築就是學生宿舍“生徒館”是當時在相當於後來的鐵道省的工部省鐵道寮任建築副長的英國人約翰·迪亞克(John Diack)主持設計的,全部英國風格不說,所有的紅磚都是壹塊壹塊地包好了從英國用軍艦運來,原價是0.2日元,要知道那年頭木匠壹天的工資也就0.1日元。運到日本後折算下來壹塊紅磚要花1.5日元以上,當時三日元能兌換二兩白銀成,就是說那些紅磚換算成現在的價格壹塊在150美元以上!
學生宿舍的豪華,生活的排場是歐洲海軍的傳統。在歐洲是貴族軍種,海軍軍官都是貴族,講究的是“Noble’s Oblige”(貴族的義務)。那意思就是國家就是妳們的,平時好吃著好喝著,到時候就得豁出去為國效力。
道格拉斯少校到了日本覺得最抓狂的壹點就是海兵的學生裏居然大多數出身農民,沒幾個貴族。出於貴族軍種的自尊心,道格拉斯在教日本人的時候最強調的就是“先成為紳士,然後才是士官(be a gentelman before the officer)”
而這點也應該是個人就挺樂意接受的。到敗戰為止,只要條件可能,日本海軍壹直維持著豪華的生活方式。軍官和士兵的夥食完全不同,正餐必須穿禮服,邊上還有軍樂隊伴奏。這點和陸軍大不壹樣,日本陸軍是有點“官兵壹致”的,起碼在戰場上,將軍和大頭兵吃的是壹樣的夥食。
海軍兵學校的學生壹進校就是壹等兵曹,相當於上士,這點和陸軍士官學校壹進校是從最下邊的二等兵開始也不同。
但要是認為海兵校僅僅是享福作樂,那就錯了。道格拉斯把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課程搬到日本來了,課本當然沒時間翻譯,也沒有必要翻譯——本來海兵校就把英語放在極高的位置上。老師是英國人,教科書是英語,用英語做作業,用英語回答問題。能用日語的地方,就只是偷偷在背後對這種“英語世界”表示不滿時發發牢騷而已,除此之外,壹切英語。當然這只是剛海兵校開始時的情形,但海兵校就壹直沒有放松對英語的要求,就是在太平洋戰爭中,軍部要求抵制英語這種“敵性語言”的時候,海兵校還是堅持連查生字用的字典都必須是英英字典。
這種訓練的效果呢?從最後的海軍次官井上成美大將戰後的謀生手段是開英語補習班教人英語這點就知道了。
江田島海兵校基本上是英國式的,但是有壹條很特別的縱向編成的“分隊”制度卻是從美國海軍學院學來的。就是由大約40人左右的三個年級學生編成,三年級學生被稱為“壹號生徒”在分隊裏起指導的作用,二年級學生是“二號生徒”幫著壹號學徒敲邊鼓,所有動手化體力的活都是被稱為“三號生徒”的壹年級新生去幹。海兵校學制三年或者是四年,所以有時還有“四號生徒”這樣壹個學生在校期間最多和前後7屆的學生朝夕相處,而海兵校除了“坐學”就是課堂教學以外,所有的生活,訓練全部以分隊為單位進行,以此來培養海軍的向心力和對先輩學生的絕對服從。
為什麽要這樣,海軍有海軍的特殊性。首先,海軍是在茫茫大海上,要活大家壹起活,船沈了大家壹起死,可以說是壹個從大頭兵到艦長長官的命運共同體;反過來說,這些大老爺們成天擠在壹個悶鐵罐子裏又是煩躁,不安和狂暴的壹個因素,因此海軍教育的第壹條就是人際關系教育,這可是人家大英帝國的皇家海軍花了上百年摸索出來的經驗。
道格拉斯少校帶給海兵校的另外壹件東西是體育運動。海兵校在1874年,首次召開了名叫“競鬥遊戲會”的運動會,這就是現在日本學校,企業等各團體每年都要開壹次的“運動會”的開始。
海軍兵學校最重要的壹點就是堅持了入學考試的嚴肅性,除了皇族成員之外,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沒有階級等級的任何限制。明治初年,也就是1870年代的日本是壹個極其貧窮落後的國家。像海軍兵學校招生公正,學費生活費全免,畢業就是國家保證終身前程的海軍軍官的去處,立即成為青年人最理想的去處之壹,所以和陸軍士官學校壹樣,海軍兵學校也能征集到最優秀的學生,海軍兵學校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在英國教官撤走以後學校的教育和管理也沒有放松,教學質量沒有下降,就這樣成為了世界三大海軍學校之壹。有了這個條件,日本海軍就能夠保證了軍官的質量。
當然海軍兵學校的教育進入了二十世紀以後實際上沒有與時並進,落後於了時代,也是日本海軍失敗的壹個原因,這點以後再說。
在培養人才的同時,海軍的組織建設也在進行。明治維新主要是在薩摩藩(現在的鹿兒島縣壹帶)和長州藩(現在的山口縣壹帶)的支持下進行的,所謂“薩長同盟”就是指的這件事。維新以後,長州藩執掌了陸軍,薩摩藩則主宰了海軍,有所謂“長州的陸軍,薩摩的海軍”的說法。日本海軍發展初期的三位主要人物,先後擔任過海軍卿,海軍大臣,主持海軍軍政的川村純義,西鄉從道和擔任過參謀本部次長,參謀本部海軍部長,主持海軍軍令仁禮景範全是薩摩人。
明治海軍最早是軍政軍令統壹的,海洋海面分成“海軍區”海軍艦船分配給分設的“鎮守府”管轄。最早是1875年在橫濱設立的“東海鎮守府”後來移到橫須賀改名為“橫須賀鎮守府”當時本來是還有個計劃設在長崎的“西海鎮守府”的,但壹直沒設立起來,倒是在1889年又加上了吳和佐世保兩個鎮守府,成為三個海軍區。1901年又設立了舞鶴鎮守府,成了四個海軍區。
原來還曾經計劃在北海道的室蘭設立壹個鎮守府,但沒有實現。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還設立了壹個旅順鎮守府,壹直到第壹次世界大戰時的1914年才撤銷。
和1878年就從陸軍省獨立出來的參謀本部相比,軍令部從海軍省獨立出來是15年後的1893年,而且壹開始的名稱還是“海軍軍令部”把“海軍”這個定語去掉又花了40年,到1933年才成了“軍令部”筆者在《軍國幕僚》中講過參謀本部從陸軍省獨立從而形成日本陸軍軍政軍令分離的來龍去脈。在陸軍軍政軍令分離的時候,海軍還沒有分離,這裏面最大的原因就是陸軍軍政軍令分離的直接引發因素是被稱為“竹橋事件”的兵變,而海軍和陸軍不同。陸軍隨便有幾個人拿了槍就能造上壹反,而海軍不是全艦壹致就開不動那艘軍艦,就算妳全艦壹致,碼頭上不給妳加煤,妳也就是個浮在水面上的鐵盒子而已,所以兵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此在壹開始軍政軍令分離時就沒有考慮海軍。
所以參謀本部獨立的時候,海軍連參謀部都還沒有,相當於參謀部的壹部分職能由海軍省軍事部在執行。日本陸軍的參謀制度和以後的軍政軍令分離是從德國引進的,而日本海軍是學的英國,所以壹開始在組織上沒有參謀部也很正常。到現在英國皇家海軍和美國海軍都沒有“參謀部”這個名字,英國皇家海軍更為邪門,雖然沒有海軍參謀部,但海軍大臣(也叫“首席海軍卿”FirstSea Lord)居然同時是“海軍總參謀長”(Chief of Naval Staff)也不知道這個“總”從何而來。
但海軍看著陸軍有個參謀本部比較眼紅,海軍軍事部也要從海軍省獨立來個“海軍參謀本部”遭到了從德國引進參謀本部制度的山縣有朋和桂太郎的堅決反對,理由是陸海戰的性質不同,陸軍是主力而海軍只是支援力量,大家壹人壹套參謀只會沒事就扯皮。陸戰是智慧的戰場,海戰只是訓練的戰場,陸將要學的多,海將只要會航海就行……反正海軍弄參謀部沒有任何必要,這不,世界上還沒有壹個國家的海軍有參謀部的。
其實陸軍的堅決反對,理由並不在表面上說的那些車軲轆話。參謀本部是天皇的幕僚部,好不容易弄到了這個位置的陸軍絕不容許海軍來分壹杯羹。當然陸軍也弄不清楚海軍到底是怎麽壹回事,這才有海軍簡直都不配弄個“參謀”的位置這壹邪門理論。據說是陸軍沒了參謀打不了仗,陸軍參謀能構思出精彩的作戰方案出來,而海軍的所謂“參謀”不就是抄抄寫寫的文書員嗎?在陸軍眼裏的海軍就是個操縱機器的工匠,完全沒有主觀能動性發揮的余地,妳的參謀再能幹,水兵訓練得再好,速度是十節的軍艦妳開不出十壹節出來,3000米射程的大炮妳打不到3100米去,海軍打仗不就是大家壹字排好了,大炮開口說話,誰的口大誰贏,有什麽“戰爭藝術性”可言,現在就這麽壹撥工匠也要學陸軍來搞什麽參謀制度,妳說可笑不可笑?
參謀部不希罕,但是諸軍種的聯合參謀部在這個世界上都是挺新的時髦玩藝。現在大名鼎鼎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其實是1942年6月20日才成立的。大國中軍種間聯合參謀部較早的是英國,成立於1939年英國的參謀長委員會(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起源也只好追溯到1923年成立的皇家防衛委員會(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就為止了。
但是壹般被認為沒有什麽創造力的日本人倒早在1886年3月就搗鼓出來過壹個“統合參謀本部”來海陸全管,但剛過兩年就又分了家。回顧壹下這壹段剛拼好鋪蓋就分炕的歷史對於了解日本海軍是很有幫助的。筆者在《有壹類戰犯叫“參謀”》裏面講過壹點那段歷史,這次從海軍的角度來看看那段歷史。
陸軍反對海軍參謀部,就連海軍都不是人人喜歡參謀部。首任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就不喜歡什麽參謀部,因為西鄉從道是陸軍出身,其實不懂海軍。他在當著海軍大臣的時候,軍銜還是陸軍中將呢,後來才混上元帥海軍大將的。當時有個從英國留學回來的海軍大尉叫黑岡帶刀的是個海軍參謀部最積極的鼓吹者,這位在1881年升了少佐又去當駐英武官的時候,說動了當時的海軍卿川村純義。在黑岡那兒,被桂太郎作為反對成立海軍參謀本部的理由,全成了應該趕快立即成立海軍參謀本部的理由:日本是海國,有了戰事海軍是先鋒,先鋒沒有了參謀本部怎麽辦?大家都是天皇陛下的戰士,人人平等,為什麽陸軍有的海軍沒有?
黑岡幹脆就來了個獅子大開口,提出幹脆來個“統合參謀本部”下分陸軍部和海軍部,參謀總長由陸海軍輪流坐莊。黑岡本來就是想用這些條件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地換取陸軍的讓步,誰知道被當時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聽進去了。伊藤博文雖然不是軍人,但利用他的聲望和人望,楞是說服了陸軍收留了海軍成立了壹個“統合參謀本部”首任參謀總長是有棲川宮熾仁親王,陸軍部長是曾我佑準陸軍中將,海軍部部長是仁禮景範海軍中將。看過《有壹類戰犯叫“參謀”》的都還記得,這彪人馬除了山縣有朋不在了幾乎就是當年在“西南戰爭”中去打西鄉隆盛賊軍的那原班人馬。
都是老相識了,應該還好打交道了吧?不,首先海軍大臣就不感冒這個倒頭的“統合參謀本部”想想也是,海軍大臣和陸軍大臣平起平坐,可是參謀總長是陸軍。這就顯得海軍要歸陸軍管了,低人壹頭。那麽陸軍該滿意了吧,也不滿意。陸軍不滿意的理由更荒唐,日本陸軍當時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區別就是在“外征軍備”這個問題上,陸軍元老山縣有朋,大山嚴全是主流派,主張擴充軍備對外戰爭。而這個參謀本部陸軍部的先後兩任部長曾我佑準和小澤武雄全是反對擴張的非主流派,“既恨和尚,禍及袈裟”主流派們捎帶著連這個位置也討厭了起來,幹脆撤了那個倒黴衙門,不給這些日奸們官做,這就弄得所謂統合參謀本部只活了兩年就壹命嗚呼了。曾我中將也被趕去了預備役。
撤銷了統合參謀本部,陸軍把“參謀本部”的大名給帶回去了,還堅決反對加上“陸軍”這壹個定語,因為《參謀本部條例》裏面明文規定:“參謀總長是帝國軍隊的參謀總長”也是妳們海軍的,幹嗎要加上壹個“陸軍”的限定語?要加妳們自己加。只能忍聲吞氣的小二子海軍在用了幾年“海軍參謀部”以後幹脆就不要“參謀”這兩個字了,叫做“海軍軍令部”和陸軍徹底劃清界限。
界限劃得非常清楚,凡陸軍的規矩海軍就不用。陸軍辦了個“陸軍大學校”說是不是陸大出身的人就不能當參謀,海軍就沒有那條規定,誰都能當參謀。
當然到了最後海軍參謀還是幾乎被海大畢業生被包圓了,但只是“幾乎”“神風攻擊隊之父”大西瀧治郎中將就考了兩次沒考上,可最後還是軍令部次長,就是說海軍沒那條硬性規定。
不管怎麽說,海軍的組織壹直到日俄戰爭之後並沒有什麽軍政軍令二元化這麽壹說,所有權力基本都在海軍省手裏,壹切都很健全,看不出有什麽很大的問題。
有了高質量的軍官,有了壹個健全的組織系統。如果再有了軍艦武器硬件,只要稍以時間,熟悉了武器裝備性能以後,壹夜之間的飛躍並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情。但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內亂不斷,到1884年為止,包括佐賀叛亂,荻叛亂,神風聯叛亂,西南戰爭等內戰和騷動什麽的合計起來居然有162起。
政府疲於奔命地到處鎮壓,軍費幾乎全部被陸軍花完,海軍在軍艦的擴充上面的要求無法滿足。所以日本海軍壹直到十九世紀70年代始終圓不了從勝海舟開始的“大海軍夢”但在1871年臺灣“牡丹社事件”以後,事情起了變化。那年10月壹艘琉球漁船在海上遭遇臺風,漂流到臺灣東南部八瑤灣,登陸的66人因和臺灣土著人發生沖突而被殺害54人,剩余12人在當地漢人求助下由大清官員轉道福州回國。
1873年明治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前往中國交涉,總理衙門行走毛昶熙壹開始的回答還像話:“二島(指琉球與臺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次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和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
但毛昶熙在看到日方出示的死者中有四位日本漁民的證據,並揚言琉球屬於日本版圖以後居然改言“(臺灣)生番系化外之民,伐與不伐,貴國自裁之。”
留給了日本壹句可以向“無主番界”出兵的話柄。
當時執掌大權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立即成立了以大隈重信為長官的藩地事務局,事務局長為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從英美急忙買了兩艘商船,裝上大炮作為軍艦,準備攻打臺灣這塊“無主番地”但和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並稱“維新三傑”的參議木戶孝永強烈反對出兵臺灣,加上英美諸列強也不同意,內閣決定延期出兵。但在長崎待命的西鄉從道拒不受命,率領三千名官兵在1874年5月2日出兵,5月6日在臺灣南部登陸。這次行動在歷史上被稱作“西鄉大暴走”開了日本軍人在近代史上“下可上”反抗政府的先河。
5月下旬,大清派船政大臣沈葆楨來臺,並調淮軍六千人赴臺作戰。後來在英國公使威妥瑪斡旋之下中日之間達成《北京專約》清廷糊裏糊塗賠了日本人50萬兩白銀不算,還承認了日軍出兵是“保民義舉”這就給了日本日後認定琉球是日本屬地的根據。第二年開始日本開始處分琉球,並在1879年強迫琉球國王移住東京。
但清廷並未放棄琉球主權,壹直到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才不再主張。
這次日軍的出兵臺灣在東亞海軍史上引起的後果就是清日兩國同時進入了擴張海軍軍備的時代。
西鄉從道在這次出兵之後感到了充實海軍軍備的必要,從陸軍中將轉到海軍中將,並且說服政府把海軍的預算提到到了陸軍的壹半。1875年當年就花了當年海軍預算的90%,311萬日元向英國訂購了“扶桑”“金剛”和“比睿”號三艘軍艦,到1878年投入現役。這三艘軍艦都不到四千噸,按當時歐洲國家所保有的萬噸左右級別的戰艦標準,實在不能算什麽戰艦,所以後來日本人自己也把這幾艘軍艦只算成“海防艦”但是在1885年北洋水師的“定遠”“鎮遠”兩艘7200噸的鐵甲艦編入現役以前這三艘軍艦壹直是亞洲國家所唯壹保有的近代化裝甲艦。
到1890年隨《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公布的《海軍條例》出臺時,日海軍已經擁有了“高千穗”“扶桑”“大和”“葛城”“武藏”和“浪速”等六艘海防艦的“常備艦隊”和壹些過時陳舊的艦只組成的“演習艦隊”1891年舉行了第壹次由常備艦隊扮演進攻壹方的“東軍”對演習艦隊扮演防守壹方的“西軍”的海軍大演習。演習後舉行了第二次海軍檢閱式,和六艘軍艦,排水2400噸的第壹次海軍檢閱式相比,這次的陣容達到了19艘軍艦,排水三萬噸,23年海軍增長了15倍。
可是面對北洋水師的“定遠”和“鎮遠”這三萬噸的海軍還是像紙糊的壹樣不堪壹擊。這就是伊東佑亨看了“定遠”和“鎮遠”後發愁的由來。於是日本舉國上下從明治天皇開始剔肉以助海軍,1893年仁禮景範海相會同樞密顧問官樺山資紀向議會提出的建造甲鐵艦兩艘,巡洋艦,輕型巡洋艦各壹艘,建造費共1955萬日元被議會否決。但2月10敕日明治天皇發布《建艦詔》內容為六年間每年減少內帑30萬日元(20萬兩白銀)文武官員壹律減俸壹成,以助海軍造艦。議會只好再次通過壹個六年內撥款1808萬日元的預算。
國民也是踴躍捐獻,終於籌起來了建造能夠和定遠和鎮遠抗衡軍艦的款項。定購了戰艦“富士”“八島”巡洋艦“明石”和“宮古”聯想到當時的西太後在滿心歡喜地要做壽,真不知道讓人說何是好。記得有壹年壹位日本教授從北京回來讓筆者去看他拍的錄像,當看到頤和園的石舫時,那教授特地加了壹句:“據說是托了這個石舫的福,日本才贏得了日清戰爭”筆者無言以對,只能期望此等悲劇不要二次重演。
但這幾艘軍艦並沒有趕上參加甲午戰爭,參加甲午戰爭的是從1888年開始的“四景艦”計劃。
為了對抗7200噸,裝甲厚度305mm,配備兩門30.5厘米雙聯炮的這兩艘巨艦,日本海軍的對策是不管怎樣,首先在大炮上要勝過定遠和鎮遠,起碼在數字上要超過去。這就是那個“四景艦”計劃。所謂“四景艦”是以日本四個觀光名地命名的四艘裝甲巡洋艦“松島”“嚴島”“橋立”和“秋津州”負責設計的法國工程師埃米爾·貝當開始時考慮到日本僅僅擁有4000噸級船塢,從而想以法國的防護巡洋艦為藍本,建造壹種配備多門中口徑火炮,增加動力性能的高速巡洋艦,但被滿腦子定遠鎮遠的日本海軍拒絕。
貝當沒辦法,只好在4000噸的船身上把32厘米單聯重炮楞塞下去。作為代價的是削減裝甲厚度和動力出力,打個比方說就是給小孩壹支大手槍。這門32厘米單聯炮只要旋轉方向或改變傾角都會使船的重心發生變化,東倒西歪,而開炮的後坐力又會使得船偏離行駛方向,就是說基本上就只能用來壯壯膽。
能壯膽就行,就這麽不由分說地在法國造了“松島”和“嚴島”到第三艘第四艘的時候,幹脆在1888年自己在橫須賀海軍造船所造了。這種國產化的措施引起了貝當的極大憤怒,在合同還沒有滿期的情況下回國,不管了。日本人到最後還是把“橋立”號造了出來,到第四艘時還是修改計劃,回到貝當開始的設計思想,造成了壹艘排水量3150噸,配備四門15.2CM單聯炮,6門12CM單聯炮和8門4.7CM單聯炮,速度達19節的高速巡洋艦。這樣原來計劃中的“四景艦”就成了“三景艦”到1894年“橋立”和“秋津州”編入現役時,日本海軍雖然還沒有和北洋水師開打必勝的把握,但自己覺得已經不那麽害怕了。
對日本來說,海軍的最後準備完成就是萬事俱備了。
東京小石川炮兵工廠的小石川後樂園。受外務大臣榎本武揚的委托,海軍大臣樺山資紀中將在這裏召開壹個遊園會形式的歡迎宴會。貴賓是大清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和正在日本訪問的包括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鎮遠號”在內的七艘軍艦上的50名大清水師軍官。
樺山資紀氣惱地對海軍次官伊藤雋吉少將說:“最討厭的就是這個丁汝昌,榎本外相硬要講什麽‘日清友好’,這樣,明天全體出動去會會這個遲早要在戰場上見面的敵人,大家都把這個丁汝昌的臉給我記住了,把軍務局長喊來。”
當時的海軍省軍務局長就是伊東佑亨少將。伊東壹進門,樺山資紀就問了他壹個問題:“伊東君,妳說丁汝昌這次為什麽走這麽條怪路,從下關進日經瀨戶內海繞紀伊半島到東京來?”
這位後來指揮著聯合艦隊大敗北洋水師,壹直晉升到元帥海軍大將的伊東少將回答說:“丁汝昌這是在向我們示威,那意思是說日本的內海就是北洋水師的庭院,如果日清開戰,他能指揮著北洋水師壹口氣攻到東京。去參加歡迎宴會沒問題,但請大臣無論如何也要懇請外務大臣和首相同意我們也去訪問壹次清國”第二天,伊東佑亨在遊園會上劈頭對丁汝昌就說:“丁提督,能不能讓我參觀壹下妳們偉大的超級戰艦‘定遠號’?”
丁汝昌坦然地笑了笑:“什麽時候都非常歡迎,但是您只能看,我們不會回答您提出的問題。”
丁汝昌有資格坦然,這艘長達95米,滿載排水量7355噸,航速16節的德國造戰艦“定遠號”是當時遠東的最大新型戰艦,裝備在“定遠號”上的兩門30.5厘米雙連炮能夠毫不容情地把所有敵艦送進海底。讓妳伊東佑亨參觀壹下又怎麽樣?
第二天伊東少將在丁汝昌的陪同下參觀了“定遠”“鎮遠”兩艦。
樺山海軍大臣在海軍省等著伊東的報告。
而伊東的報告是:“如果現在和清國開戰,我們沒有勝利的可能,只要‘定遠’和‘鎮遠’兩艦就能把全部常備艦隊送到海底。閣下,軍艦,我們要軍艦,我們是四面環海的海國,衛國就是衛海,擁有能和‘定遠’對抗的軍艦是我們最要緊的。”
樺山嘆了壹口氣:“李鴻章的目的達到了”被稱為海軍的“頭腦”位居軍務局長,實際上指揮著日本海軍的伊東佑亨被逼著說出來了“沒有勝利的可能”李鴻章派丁汝昌率北洋水師訪日的目的——向日本示威的目的,確確實實地達到了。
其實,在這之前5年,1886年的8月,北洋水師就派出以“定遠”“鎮遠”兩艘主力巡洋艦為首的四艘軍艦(還有兩艘是“濟遠”和“威遠”訪問過日本,帶隊的還是丁汝昌,那次是在黃海演習完畢以後,開到長崎去修理軍艦去的。修理軍艦也沒有必要到日本去,所以其實有個七八成炫耀武力的成分在裏面。但那次的長崎寄港鬧出了壹個在日本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的“清國長崎水兵事件”北洋水師士兵因為嫖妓和日本警察發生沖突,雙方大打出手,死10人,傷70余人,結果是日本人賠禮道歉,賠償損失了事)。
時隔五年,北洋水師雖然沒有增加新艦新炮,但還是讓伊東佑亨垂頭喪氣。
但有人不這麽看。
回航時北洋水師還是走瀨戶內海,在廣島的宮島錨泊時,接受了吳鎮守府長官中牟田倉之助中將和參謀長東鄉平八郎大佐的訪問。在這次訪問“平遠號”聲稱故障,進入吳軍港檢修,其實是有點觀察和偵查日本海軍技術程度的意思。
但是結果是北洋水師的底細被人家摸了個底掉。
東鄉平八郎大佐幾乎每天不是軍服就是便服在碼頭觀察“平遠號”最後的結論是:“清國艦隊不足為慮,他們只是壹把褪了火的寶刀。寶刀確實是寶刀,但是已經褪了火,真正需要的時候派不上用場”為什麽這麽說呢?用東鄉的原話:“神聖的炮口上,掛了不少東西,從內褲到襪子什麽都有,怎麽看怎麽像晾衣桿,這還是在外國的港口呢,甲板上也是亂七八糟,根本就沒有整理”“炮口是軍艦的靈魂,從清國艦隊能夠毫無顧慮地這樣做就知道這支艦隊的士氣,從軍官到士兵沒有任何緊張感,軍艦本來所具有的力量發揮不了,沒什麽可怕的”這是在說海軍的軟件,沒有配套的軟件,光有硬件是不能被稱為海軍的。
東鄉平八郎看出了北洋水師是軟件配套沒有趕上硬件購置。
但日本海軍呢?在這方面不得不承認日本海軍的建設是先從軟件建設開始的。
19世紀後半期的日本是壹個落後的農業國,為什麽能像變戲法壹樣出現了壹支包括陸海軍的很強大的軍隊?應該歸功於日本的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兵學校這兩個培養軍事指揮官的軍事院校的辦校成功。
明治二年(1869年)兵部省在《應該創立大海軍的建議》中是這麽說的:“軍艦因為士官才有精神,沒有士官,則水夫將無所作為。水夫無所作為,則艦船也就成無用的廢物。而海軍士官所必須掌握的深奧學術的練成絕非容易之事,所以當前壹大緊要事項就是盡快創辦學校。”
建設壹支海軍,需要的東西很多,比如起碼要有軍艦,要有操縱軍艦的人員和這些人員如何構成的組織。壹般來說這三要素裏最引人註目的就是軍艦,但其實軍艦問題其實最好辦,最簡單。只要拿得出錢,什麽都能買的到。當時英國,法國,德國,俄國還有美國全都在亞洲膘著勁明爭暗鬥,什麽最新式的軍艦都買得到,困難其實是人員培養訓練和編成控制。
在伊東佑亨大發沒有軍艦的感嘆時,日本海軍已經花了二十幾年的時間來努力培養和組織海軍人材了,而且這種努力的效果已經到了初見成效的時候。
1870年,明治政府模仿幕府的“長崎海軍教習所”在東京的築地開設了“海軍操練所”第二年改名為“海軍兵學寮”到1876年改名為“海軍兵學校”1888年搬到了廣島縣的江田島,在東京的海軍兵學校原址上辦了海軍大學校。中國人通常把在江田島的海軍兵學校稱為“江田島海軍學校”這要歸功於林立果在《五七壹工程紀要》裏使用了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電影《啊,海軍》裏面的翻譯。
海軍兵學寮和陸軍士官學校的前身“兵學寮”同時設立,可改名字比陸軍晚了兩年,這麽壹來“士官”這個詞被陸軍用了去,只好湊合著用“兵學”這個學究氣十足的詞了。其實陸軍有點怪,在除了“陸軍士官學校”這個校名之外再也不用這個詞,用的是“將校”可是海軍除了學校名不用“士官”這個詞以外在其他場合則是大量使用這個詞。
在日本海軍術語中,“士官”不是指的“下士官”而是相對於“士兵”而言的反義詞,也就是“軍官”的意思。少尉是“士官”大將也是“士官”日本陸軍1887年開始從法國式轉為普魯士式教育。海軍的轉型更早,從海軍操練所設立開始就從原來的法國式教育轉到了英國式。1873年開始英國派出以後來壹直做到北美艦隊上將司令官的道格拉斯(Douglas,Sir ArchibaldLucius)少校為首的34名教官來日本,英國人在日本壹呆就是17年,合計69人次,道格拉斯本人就在日本呆了兩年,如果不是有人警告他如果再趕緊不回國可能會影響到晉升的話,可能還會繼續逗留下去。
海軍兵學校和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英國達特茅斯皇家海軍學院壹起同列被譽為世界三大海軍學校,因為曾幾何時這是三大海軍強國,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仔細想壹下還是有點不可思議,和精神要素占得更多的陸軍相比,海軍更加受到國力的制約,這個海軍兵學校既然是海軍的壹部分就也應該不例外。貧窮的日本是如何辦出這個海軍兵學校的?
當時的日本是壹個很窮的落後小國,培養海軍人才最簡單而又便宜的方法應該是送人去歐美留學。其實在壹開始日本人也是那麽想的,比如東鄉平八郎就被送去英國留學,還壹去就是八年。
但是有壹點弄不明白的事情是:日本的海軍留學生到處被人拒絕,是看不起這些黃皮猴子還是為了保守海軍機密沒人知道,反正就是到哪兒哪兒不要。
像東鄉平八郎想去英國進達特茅斯皇家海軍學院,結果到了那兒別人才對他說不行,結果只能上商船學校。
沒辦法才只好從壹開始就自己辦學校,而且還是斥巨資全部請英國人來幫忙。當然英國是當時第壹海軍大國是日本人為什麽請英國人的最主要原因,更加直接的原因就是在1863年的薩英戰爭中知道了英國海軍的厲害。
1862年在現在的橫濱市生麥地方發生了所謂“生麥事件”四個英國人騎馬沖撞了薩摩藩主島津久光的行列。其實就在事情發生前幾分鐘,美國領事館官員範李德也遇到了這個行列,按照歐洲人見了貴族或婦女的馬車要下馬讓路的禮貌,範李德讓了路,沒有出事。但這幾個英國人在中國上海呆過很長時間,騎在馬上鞭打黃種人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大鼻子怎麽能給黃皮膚的日本人讓路?於是和藩主的武士發生了沖突,壹個叫理查遜的英國人被日本人把腸子砍出來了,拖著腸子想逃跑,另壹位武士“看到他很痛苦,就幫他做了介錯”壹刀把理查遜的腦袋砍下來了。兩個重傷,剩下壹個是個女的,叫波羅黛兒,倒是沒受傷,但給嚇瘋了,不久也死了。
約翰牛們很吃驚,這是他們第壹次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大英帝國的臣民也是可以被人砍殺的,而且是黃種人。於是就去找幕府論理,要幕府賠錢10萬英鎊。幕府給來了個壹問三不知:那是薩摩藩,妳得找他們。於是英國人就出動了10艘軍艦上鹿兒島來討說法來了。
英國人到了鹿兒島,看看這麽個鄉下地方,料想也拿不出10萬英鎊,就減到了二萬五,但要處分肇事者。遇到翻譯又差勁,把“肇事者”給翻成了日語的“責任者”藩主島津久光壹看急了眼:八格丫魯,要處分老爺?老爺跟妳拼了吧。這就打了起來,壹仗打下來,全日本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薩摩藩取得的壹點成果全部毀於英軍炮火,但死人不多,才五人。而反過來看來勢洶洶的英國人卻死傷63人,包括旗艦尤裏亞勒斯(HMS Euryalus)艦長約瑟林副艦長魏爾默全去見了上帝。
怎麽會打出這麽個怪結果來?其實那天可能上帝沒玩過天照大神,對英國人有點不公平。首先炮戰剛開始時海上風浪大作,英國軍艦顛簸得厲害,無法瞄準,對薩摩藩的海岸炮臺無法造成損傷。而英國艦隊停泊的地方又正好是薩摩藩炮臺平時訓練時停靶船的,這樣薩摩炮臺練瞄準都省了,壹炮打出去就直接命中英軍旗艦。
但隨著天氣變好,英國軍艦上配備的最新式阿姆斯特朗炮的威力就顯示出來了。薩摩藩的海岸炮臺被敲了個精光不說,剛剛建成的造船廠和其他近代工業全完了蛋,這才兩家人坐下來談判。
後來薩摩藩還是賠了兩萬五千英鎊,但不是薩摩藩自己的錢,向幕府借了六萬三千兩銀子賠了英國人以後就沒還,賴掉了那筆帳。
大山嚴,黑田清隆,東鄉平八郎全是參加過那場戰爭的,因此大家全同意要辦海軍,除了向英國學習外沒有別的出路這種說法。
日本人在薩英戰爭中看著英國人耍酷,眼饞得口水支流還不光是軍艦大炮和海軍。日本人發現英國人打仗時甲板上有軍樂隊在奏樂,認為非常地妙。這邊談判還沒有探出結果,那邊就有人爬到英國軍艦上要人家教他們玩洋鼓洋號,回來自己就練了起來,後來日本海軍的大型艦只上壹直有軍樂隊的編制,平時在艦上練練樂器兼管打掃衛生,戰時運運炮彈兼管吹吹打打,由來就是從薩英戰爭裏跟英國人學的。
日本人辦這個學校是很認真的,認真到了什麽程度呢?連為什麽海軍兵學校會搬到廣島的江田島區都能夠說明問題。隨著經濟的逐步繁榮,海軍省認為學校辦在繁華的東京會引起學生們思想墮落,所以才找了這個當時是鳥都不來做巢的廣島荒島,遷校之前還和當地豪紳簽訂了壹個名為《江田島取締方始末書》的合同,裏面規定在江田島指定範圍內不得有“猥藝醜行”就是說不能開娼館妓院,以保持教育環境。而壹直到1945年日本敗戰為止的57年間江田島還確實是做到了這壹點。至於到後來設施被美軍接收,飛燕流鶯從全日本和全世界各地雲集江田島,繁榮娼盛則是以後的事情了。
和所有海軍名校壹樣,江田島海軍兵學校最豪華的建築就是學生宿舍“生徒館”是當時在相當於後來的鐵道省的工部省鐵道寮任建築副長的英國人約翰·迪亞克(John Diack)主持設計的,全部英國風格不說,所有的紅磚都是壹塊壹塊地包好了從英國用軍艦運來,原價是0.2日元,要知道那年頭木匠壹天的工資也就0.1日元。運到日本後折算下來壹塊紅磚要花1.5日元以上,當時三日元能兌換二兩白銀成,就是說那些紅磚換算成現在的價格壹塊在150美元以上!
學生宿舍的豪華,生活的排場是歐洲海軍的傳統。在歐洲是貴族軍種,海軍軍官都是貴族,講究的是“Noble’s Oblige”(貴族的義務)。那意思就是國家就是妳們的,平時好吃著好喝著,到時候就得豁出去為國效力。
道格拉斯少校到了日本覺得最抓狂的壹點就是海兵的學生裏居然大多數出身農民,沒幾個貴族。出於貴族軍種的自尊心,道格拉斯在教日本人的時候最強調的就是“先成為紳士,然後才是士官(be a gentelman before the officer)”
而這點也應該是個人就挺樂意接受的。到敗戰為止,只要條件可能,日本海軍壹直維持著豪華的生活方式。軍官和士兵的夥食完全不同,正餐必須穿禮服,邊上還有軍樂隊伴奏。這點和陸軍大不壹樣,日本陸軍是有點“官兵壹致”的,起碼在戰場上,將軍和大頭兵吃的是壹樣的夥食。
海軍兵學校的學生壹進校就是壹等兵曹,相當於上士,這點和陸軍士官學校壹進校是從最下邊的二等兵開始也不同。
但要是認為海兵校僅僅是享福作樂,那就錯了。道格拉斯把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課程搬到日本來了,課本當然沒時間翻譯,也沒有必要翻譯——本來海兵校就把英語放在極高的位置上。老師是英國人,教科書是英語,用英語做作業,用英語回答問題。能用日語的地方,就只是偷偷在背後對這種“英語世界”表示不滿時發發牢騷而已,除此之外,壹切英語。當然這只是剛海兵校開始時的情形,但海兵校就壹直沒有放松對英語的要求,就是在太平洋戰爭中,軍部要求抵制英語這種“敵性語言”的時候,海兵校還是堅持連查生字用的字典都必須是英英字典。
這種訓練的效果呢?從最後的海軍次官井上成美大將戰後的謀生手段是開英語補習班教人英語這點就知道了。
江田島海兵校基本上是英國式的,但是有壹條很特別的縱向編成的“分隊”制度卻是從美國海軍學院學來的。就是由大約40人左右的三個年級學生編成,三年級學生被稱為“壹號生徒”在分隊裏起指導的作用,二年級學生是“二號生徒”幫著壹號學徒敲邊鼓,所有動手化體力的活都是被稱為“三號生徒”的壹年級新生去幹。海兵校學制三年或者是四年,所以有時還有“四號生徒”這樣壹個學生在校期間最多和前後7屆的學生朝夕相處,而海兵校除了“坐學”就是課堂教學以外,所有的生活,訓練全部以分隊為單位進行,以此來培養海軍的向心力和對先輩學生的絕對服從。
為什麽要這樣,海軍有海軍的特殊性。首先,海軍是在茫茫大海上,要活大家壹起活,船沈了大家壹起死,可以說是壹個從大頭兵到艦長長官的命運共同體;反過來說,這些大老爺們成天擠在壹個悶鐵罐子裏又是煩躁,不安和狂暴的壹個因素,因此海軍教育的第壹條就是人際關系教育,這可是人家大英帝國的皇家海軍花了上百年摸索出來的經驗。
道格拉斯少校帶給海兵校的另外壹件東西是體育運動。海兵校在1874年,首次召開了名叫“競鬥遊戲會”的運動會,這就是現在日本學校,企業等各團體每年都要開壹次的“運動會”的開始。
海軍兵學校最重要的壹點就是堅持了入學考試的嚴肅性,除了皇族成員之外,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沒有階級等級的任何限制。明治初年,也就是1870年代的日本是壹個極其貧窮落後的國家。像海軍兵學校招生公正,學費生活費全免,畢業就是國家保證終身前程的海軍軍官的去處,立即成為青年人最理想的去處之壹,所以和陸軍士官學校壹樣,海軍兵學校也能征集到最優秀的學生,海軍兵學校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在英國教官撤走以後學校的教育和管理也沒有放松,教學質量沒有下降,就這樣成為了世界三大海軍學校之壹。有了這個條件,日本海軍就能夠保證了軍官的質量。
當然海軍兵學校的教育進入了二十世紀以後實際上沒有與時並進,落後於了時代,也是日本海軍失敗的壹個原因,這點以後再說。
在培養人才的同時,海軍的組織建設也在進行。明治維新主要是在薩摩藩(現在的鹿兒島縣壹帶)和長州藩(現在的山口縣壹帶)的支持下進行的,所謂“薩長同盟”就是指的這件事。維新以後,長州藩執掌了陸軍,薩摩藩則主宰了海軍,有所謂“長州的陸軍,薩摩的海軍”的說法。日本海軍發展初期的三位主要人物,先後擔任過海軍卿,海軍大臣,主持海軍軍政的川村純義,西鄉從道和擔任過參謀本部次長,參謀本部海軍部長,主持海軍軍令仁禮景範全是薩摩人。
明治海軍最早是軍政軍令統壹的,海洋海面分成“海軍區”海軍艦船分配給分設的“鎮守府”管轄。最早是1875年在橫濱設立的“東海鎮守府”後來移到橫須賀改名為“橫須賀鎮守府”當時本來是還有個計劃設在長崎的“西海鎮守府”的,但壹直沒設立起來,倒是在1889年又加上了吳和佐世保兩個鎮守府,成為三個海軍區。1901年又設立了舞鶴鎮守府,成了四個海軍區。
原來還曾經計劃在北海道的室蘭設立壹個鎮守府,但沒有實現。1905年日俄戰爭以後還設立了壹個旅順鎮守府,壹直到第壹次世界大戰時的1914年才撤銷。
和1878年就從陸軍省獨立出來的參謀本部相比,軍令部從海軍省獨立出來是15年後的1893年,而且壹開始的名稱還是“海軍軍令部”把“海軍”這個定語去掉又花了40年,到1933年才成了“軍令部”筆者在《軍國幕僚》中講過參謀本部從陸軍省獨立從而形成日本陸軍軍政軍令分離的來龍去脈。在陸軍軍政軍令分離的時候,海軍還沒有分離,這裏面最大的原因就是陸軍軍政軍令分離的直接引發因素是被稱為“竹橋事件”的兵變,而海軍和陸軍不同。陸軍隨便有幾個人拿了槍就能造上壹反,而海軍不是全艦壹致就開不動那艘軍艦,就算妳全艦壹致,碼頭上不給妳加煤,妳也就是個浮在水面上的鐵盒子而已,所以兵變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此在壹開始軍政軍令分離時就沒有考慮海軍。
所以參謀本部獨立的時候,海軍連參謀部都還沒有,相當於參謀部的壹部分職能由海軍省軍事部在執行。日本陸軍的參謀制度和以後的軍政軍令分離是從德國引進的,而日本海軍是學的英國,所以壹開始在組織上沒有參謀部也很正常。到現在英國皇家海軍和美國海軍都沒有“參謀部”這個名字,英國皇家海軍更為邪門,雖然沒有海軍參謀部,但海軍大臣(也叫“首席海軍卿”FirstSea Lord)居然同時是“海軍總參謀長”(Chief of Naval Staff)也不知道這個“總”從何而來。
但海軍看著陸軍有個參謀本部比較眼紅,海軍軍事部也要從海軍省獨立來個“海軍參謀本部”遭到了從德國引進參謀本部制度的山縣有朋和桂太郎的堅決反對,理由是陸海戰的性質不同,陸軍是主力而海軍只是支援力量,大家壹人壹套參謀只會沒事就扯皮。陸戰是智慧的戰場,海戰只是訓練的戰場,陸將要學的多,海將只要會航海就行……反正海軍弄參謀部沒有任何必要,這不,世界上還沒有壹個國家的海軍有參謀部的。
其實陸軍的堅決反對,理由並不在表面上說的那些車軲轆話。參謀本部是天皇的幕僚部,好不容易弄到了這個位置的陸軍絕不容許海軍來分壹杯羹。當然陸軍也弄不清楚海軍到底是怎麽壹回事,這才有海軍簡直都不配弄個“參謀”的位置這壹邪門理論。據說是陸軍沒了參謀打不了仗,陸軍參謀能構思出精彩的作戰方案出來,而海軍的所謂“參謀”不就是抄抄寫寫的文書員嗎?在陸軍眼裏的海軍就是個操縱機器的工匠,完全沒有主觀能動性發揮的余地,妳的參謀再能幹,水兵訓練得再好,速度是十節的軍艦妳開不出十壹節出來,3000米射程的大炮妳打不到3100米去,海軍打仗不就是大家壹字排好了,大炮開口說話,誰的口大誰贏,有什麽“戰爭藝術性”可言,現在就這麽壹撥工匠也要學陸軍來搞什麽參謀制度,妳說可笑不可笑?
參謀部不希罕,但是諸軍種的聯合參謀部在這個世界上都是挺新的時髦玩藝。現在大名鼎鼎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其實是1942年6月20日才成立的。大國中軍種間聯合參謀部較早的是英國,成立於1939年英國的參謀長委員會(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起源也只好追溯到1923年成立的皇家防衛委員會(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就為止了。
但是壹般被認為沒有什麽創造力的日本人倒早在1886年3月就搗鼓出來過壹個“統合參謀本部”來海陸全管,但剛過兩年就又分了家。回顧壹下這壹段剛拼好鋪蓋就分炕的歷史對於了解日本海軍是很有幫助的。筆者在《有壹類戰犯叫“參謀”》裏面講過壹點那段歷史,這次從海軍的角度來看看那段歷史。
陸軍反對海軍參謀部,就連海軍都不是人人喜歡參謀部。首任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就不喜歡什麽參謀部,因為西鄉從道是陸軍出身,其實不懂海軍。他在當著海軍大臣的時候,軍銜還是陸軍中將呢,後來才混上元帥海軍大將的。當時有個從英國留學回來的海軍大尉叫黑岡帶刀的是個海軍參謀部最積極的鼓吹者,這位在1881年升了少佐又去當駐英武官的時候,說動了當時的海軍卿川村純義。在黑岡那兒,被桂太郎作為反對成立海軍參謀本部的理由,全成了應該趕快立即成立海軍參謀本部的理由:日本是海國,有了戰事海軍是先鋒,先鋒沒有了參謀本部怎麽辦?大家都是天皇陛下的戰士,人人平等,為什麽陸軍有的海軍沒有?
黑岡幹脆就來了個獅子大開口,提出幹脆來個“統合參謀本部”下分陸軍部和海軍部,參謀總長由陸海軍輪流坐莊。黑岡本來就是想用這些條件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地換取陸軍的讓步,誰知道被當時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聽進去了。伊藤博文雖然不是軍人,但利用他的聲望和人望,楞是說服了陸軍收留了海軍成立了壹個“統合參謀本部”首任參謀總長是有棲川宮熾仁親王,陸軍部長是曾我佑準陸軍中將,海軍部部長是仁禮景範海軍中將。看過《有壹類戰犯叫“參謀”》的都還記得,這彪人馬除了山縣有朋不在了幾乎就是當年在“西南戰爭”中去打西鄉隆盛賊軍的那原班人馬。
都是老相識了,應該還好打交道了吧?不,首先海軍大臣就不感冒這個倒頭的“統合參謀本部”想想也是,海軍大臣和陸軍大臣平起平坐,可是參謀總長是陸軍。這就顯得海軍要歸陸軍管了,低人壹頭。那麽陸軍該滿意了吧,也不滿意。陸軍不滿意的理由更荒唐,日本陸軍當時分成“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區別就是在“外征軍備”這個問題上,陸軍元老山縣有朋,大山嚴全是主流派,主張擴充軍備對外戰爭。而這個參謀本部陸軍部的先後兩任部長曾我佑準和小澤武雄全是反對擴張的非主流派,“既恨和尚,禍及袈裟”主流派們捎帶著連這個位置也討厭了起來,幹脆撤了那個倒黴衙門,不給這些日奸們官做,這就弄得所謂統合參謀本部只活了兩年就壹命嗚呼了。曾我中將也被趕去了預備役。
撤銷了統合參謀本部,陸軍把“參謀本部”的大名給帶回去了,還堅決反對加上“陸軍”這壹個定語,因為《參謀本部條例》裏面明文規定:“參謀總長是帝國軍隊的參謀總長”也是妳們海軍的,幹嗎要加上壹個“陸軍”的限定語?要加妳們自己加。只能忍聲吞氣的小二子海軍在用了幾年“海軍參謀部”以後幹脆就不要“參謀”這兩個字了,叫做“海軍軍令部”和陸軍徹底劃清界限。
界限劃得非常清楚,凡陸軍的規矩海軍就不用。陸軍辦了個“陸軍大學校”說是不是陸大出身的人就不能當參謀,海軍就沒有那條規定,誰都能當參謀。
當然到了最後海軍參謀還是幾乎被海大畢業生被包圓了,但只是“幾乎”“神風攻擊隊之父”大西瀧治郎中將就考了兩次沒考上,可最後還是軍令部次長,就是說海軍沒那條硬性規定。
不管怎麽說,海軍的組織壹直到日俄戰爭之後並沒有什麽軍政軍令二元化這麽壹說,所有權力基本都在海軍省手裏,壹切都很健全,看不出有什麽很大的問題。
有了高質量的軍官,有了壹個健全的組織系統。如果再有了軍艦武器硬件,只要稍以時間,熟悉了武器裝備性能以後,壹夜之間的飛躍並不是什麽不可能的事情。但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內亂不斷,到1884年為止,包括佐賀叛亂,荻叛亂,神風聯叛亂,西南戰爭等內戰和騷動什麽的合計起來居然有162起。
政府疲於奔命地到處鎮壓,軍費幾乎全部被陸軍花完,海軍在軍艦的擴充上面的要求無法滿足。所以日本海軍壹直到十九世紀70年代始終圓不了從勝海舟開始的“大海軍夢”但在1871年臺灣“牡丹社事件”以後,事情起了變化。那年10月壹艘琉球漁船在海上遭遇臺風,漂流到臺灣東南部八瑤灣,登陸的66人因和臺灣土著人發生沖突而被殺害54人,剩余12人在當地漢人求助下由大清官員轉道福州回國。
1873年明治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前往中國交涉,總理衙門行走毛昶熙壹開始的回答還像話:“二島(指琉球與臺灣)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次固在於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和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
但毛昶熙在看到日方出示的死者中有四位日本漁民的證據,並揚言琉球屬於日本版圖以後居然改言“(臺灣)生番系化外之民,伐與不伐,貴國自裁之。”
留給了日本壹句可以向“無主番界”出兵的話柄。
當時執掌大權的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立即成立了以大隈重信為長官的藩地事務局,事務局長為陸軍中將西鄉從道,從英美急忙買了兩艘商船,裝上大炮作為軍艦,準備攻打臺灣這塊“無主番地”但和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並稱“維新三傑”的參議木戶孝永強烈反對出兵臺灣,加上英美諸列強也不同意,內閣決定延期出兵。但在長崎待命的西鄉從道拒不受命,率領三千名官兵在1874年5月2日出兵,5月6日在臺灣南部登陸。這次行動在歷史上被稱作“西鄉大暴走”開了日本軍人在近代史上“下可上”反抗政府的先河。
5月下旬,大清派船政大臣沈葆楨來臺,並調淮軍六千人赴臺作戰。後來在英國公使威妥瑪斡旋之下中日之間達成《北京專約》清廷糊裏糊塗賠了日本人50萬兩白銀不算,還承認了日軍出兵是“保民義舉”這就給了日本日後認定琉球是日本屬地的根據。第二年開始日本開始處分琉球,並在1879年強迫琉球國王移住東京。
但清廷並未放棄琉球主權,壹直到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才不再主張。
這次日軍的出兵臺灣在東亞海軍史上引起的後果就是清日兩國同時進入了擴張海軍軍備的時代。
西鄉從道在這次出兵之後感到了充實海軍軍備的必要,從陸軍中將轉到海軍中將,並且說服政府把海軍的預算提到到了陸軍的壹半。1875年當年就花了當年海軍預算的90%,311萬日元向英國訂購了“扶桑”“金剛”和“比睿”號三艘軍艦,到1878年投入現役。這三艘軍艦都不到四千噸,按當時歐洲國家所保有的萬噸左右級別的戰艦標準,實在不能算什麽戰艦,所以後來日本人自己也把這幾艘軍艦只算成“海防艦”但是在1885年北洋水師的“定遠”“鎮遠”兩艘7200噸的鐵甲艦編入現役以前這三艘軍艦壹直是亞洲國家所唯壹保有的近代化裝甲艦。
到1890年隨《大日本帝國憲法》同時公布的《海軍條例》出臺時,日海軍已經擁有了“高千穗”“扶桑”“大和”“葛城”“武藏”和“浪速”等六艘海防艦的“常備艦隊”和壹些過時陳舊的艦只組成的“演習艦隊”1891年舉行了第壹次由常備艦隊扮演進攻壹方的“東軍”對演習艦隊扮演防守壹方的“西軍”的海軍大演習。演習後舉行了第二次海軍檢閱式,和六艘軍艦,排水2400噸的第壹次海軍檢閱式相比,這次的陣容達到了19艘軍艦,排水三萬噸,23年海軍增長了15倍。
可是面對北洋水師的“定遠”和“鎮遠”這三萬噸的海軍還是像紙糊的壹樣不堪壹擊。這就是伊東佑亨看了“定遠”和“鎮遠”後發愁的由來。於是日本舉國上下從明治天皇開始剔肉以助海軍,1893年仁禮景範海相會同樞密顧問官樺山資紀向議會提出的建造甲鐵艦兩艘,巡洋艦,輕型巡洋艦各壹艘,建造費共1955萬日元被議會否決。但2月10敕日明治天皇發布《建艦詔》內容為六年間每年減少內帑30萬日元(20萬兩白銀)文武官員壹律減俸壹成,以助海軍造艦。議會只好再次通過壹個六年內撥款1808萬日元的預算。
國民也是踴躍捐獻,終於籌起來了建造能夠和定遠和鎮遠抗衡軍艦的款項。定購了戰艦“富士”“八島”巡洋艦“明石”和“宮古”聯想到當時的西太後在滿心歡喜地要做壽,真不知道讓人說何是好。記得有壹年壹位日本教授從北京回來讓筆者去看他拍的錄像,當看到頤和園的石舫時,那教授特地加了壹句:“據說是托了這個石舫的福,日本才贏得了日清戰爭”筆者無言以對,只能期望此等悲劇不要二次重演。
但這幾艘軍艦並沒有趕上參加甲午戰爭,參加甲午戰爭的是從1888年開始的“四景艦”計劃。
為了對抗7200噸,裝甲厚度305mm,配備兩門30.5厘米雙聯炮的這兩艘巨艦,日本海軍的對策是不管怎樣,首先在大炮上要勝過定遠和鎮遠,起碼在數字上要超過去。這就是那個“四景艦”計劃。所謂“四景艦”是以日本四個觀光名地命名的四艘裝甲巡洋艦“松島”“嚴島”“橋立”和“秋津州”負責設計的法國工程師埃米爾·貝當開始時考慮到日本僅僅擁有4000噸級船塢,從而想以法國的防護巡洋艦為藍本,建造壹種配備多門中口徑火炮,增加動力性能的高速巡洋艦,但被滿腦子定遠鎮遠的日本海軍拒絕。
貝當沒辦法,只好在4000噸的船身上把32厘米單聯重炮楞塞下去。作為代價的是削減裝甲厚度和動力出力,打個比方說就是給小孩壹支大手槍。這門32厘米單聯炮只要旋轉方向或改變傾角都會使船的重心發生變化,東倒西歪,而開炮的後坐力又會使得船偏離行駛方向,就是說基本上就只能用來壯壯膽。
能壯膽就行,就這麽不由分說地在法國造了“松島”和“嚴島”到第三艘第四艘的時候,幹脆在1888年自己在橫須賀海軍造船所造了。這種國產化的措施引起了貝當的極大憤怒,在合同還沒有滿期的情況下回國,不管了。日本人到最後還是把“橋立”號造了出來,到第四艘時還是修改計劃,回到貝當開始的設計思想,造成了壹艘排水量3150噸,配備四門15.2CM單聯炮,6門12CM單聯炮和8門4.7CM單聯炮,速度達19節的高速巡洋艦。這樣原來計劃中的“四景艦”就成了“三景艦”到1894年“橋立”和“秋津州”編入現役時,日本海軍雖然還沒有和北洋水師開打必勝的把握,但自己覺得已經不那麽害怕了。
對日本來說,海軍的最後準備完成就是萬事俱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