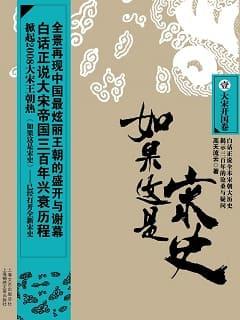- [ 免費 ] 第壹章 前因――我本亂世壹根 ...
- [ 免費 ] 第二章 凍不死的種子
- [ 免費 ] 第三章 皇帝流水線
- [ 免費 ] 第四章 讓天下人都簽投名狀 ...
- [ 免費 ] 第五章 壹個員工是怎樣折磨自 ...
- [ 免費 ] 第六章 天下英雄他最強 ...
- [ 免費 ] 第七章 馮道之殤
- [ 免費 ] 第八章 第壹戰將趙匡胤 ...
- [ 免費 ] 第九章 隕落的太陽
- [ 免費 ] 第十章 機關算盡傷聰明 ...
- [ 免費 ] 第十壹章 北宋誕生記
- [ 免費 ] 第十二章 請註意,現在我是皇 ...
- [ 免費 ] 第十三章 我的江山我裝修 ...
- [ 免費 ] 第十四章 我有壹個夢想 ...
- [ 免費 ] 第十五章 六十六天平後蜀 ...
- [ 免費 ] 第十六章 勝利者的規矩 ...
- [ 免費 ] 第十七章 愛我的間諜
- [ 免費 ] 第十八章 啊……天殺的城墻 ...
- [ 免費 ] 第十九章 宋朝的內核
- [ 免費 ] 第二十章 對這個雜種要毫不留 ...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寄生胎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 我的名字叫李煜 ...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 五字錯千年 ...
- [ 免費 ] 第二十四章 燭光搖曳話當年 ...
- [ 免費 ] 第二十五章 魂歸洛陽川 ...
- [ 免費 ] 第壹章 天下不過二三事 ...
- [ 免費 ] 第二章 春水向金陵
- [ 免費 ] 第三章 命運之巔 睥睨天下 ...
- [ 免費 ] 第四章 如果這是契丹
- [ 免費 ] 第五章 壹夜夢燕雲
- [ 免費 ] 第六章 劇痛的心靈
- [ 免費 ] 第七章 所謂名相
- [ 免費 ] 第八章 百年之錯
- [ 免費 ] 第九章 天國逆子
- [ 免費 ] 第十章 契丹,朕賭妳的全部! ...
- [ 免費 ] 第十壹章 大宋名相第壹人 ...
- [ 免費 ] 第十二章 痛烈人生 屹立不倒 ...
- [ 免費 ] 第十三章 生死萬歲殿
- [ 免費 ] 第十四章 啊……衰神
- [ 免費 ] 第十五章 溫暖貼心王愛卿 ...
- [ 免費 ] 第十六章 開業大吉 昏天黑地 ...
- [ 免費 ] 第十七章 李繼遷時刻
- [ 免費 ] 第十八章 我寇準又殺回來了! ...
- [ 免費 ] 第十九章 豺狼的末日
- [ 免費 ] 第二十章 天不滅趙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澶淵……澶淵!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 天書降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 聖祖臨
- [ 免費 ] 第二十四章 大宋官場眾生相 ...
- [ 免費 ] 第二十五章 宋朝的味道 ...
- [ 免費 ] 第壹章 宋朝能否不姓趙 ...
- [ 免費 ] 第二章 老冤家寇準、李迪 ...
- [ 免費 ] 第三章 趙恒建陵
- [ 免費 ] 第四章 丁謂的高度
- [ 免費 ] 第五章 生死兩艱難
- [ 免費 ] 第六章 三國少年說
- [ 免費 ] 第七章 宋朝邊帥曹瑋
- [ 免費 ] 第八章 趙恒剛登基
- [ 免費 ] 第九章 王欽若之死
- [ 免費 ] 第十章 太後的幸與不幸 ...
- [ 免費 ] 第十壹章 祭天祭祖
- [ 免費 ] 第十二章 怨恨變毒藥
- [ 免費 ] 第十三章 呂夷簡做到了 ...
- [ 免費 ] 第十四章 媽媽,我想妳 ...
- [ 免費 ] 第十五章 壹份超級榮譽 ...
- [ 免費 ] 第十六章 西夏孵化記
- [ 免費 ] 第十七章 史上最隆重離婚 ...
- [ 免費 ] 第十八章 廢後自有故事 ...
- [ 免費 ] 第十九章 楷模趙光義
- [ 免費 ] 第二十章 開封青雲路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不能打壓,試試賄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 三百年間他第壹 ...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 範仲淹和他的朋友 ...
- [ 免費 ] 第二十四章 黨項人的發家史 ...
- [ 免費 ] 第二十五章 誰是首相
- [ 免費 ] 第二十六章 黑暗前的黎明 ...
- [ 免費 ] 第二十七章 必勝的信號 ...
- [ 免費 ] 第二十八章 李元昊的痛苦—— ...
- [ 免費 ] 第二十九章 士兵們的潛臺詞 ...
- [ 免費 ] 第三十章 超級絕望的現實 ...
- [ 免費 ] 第三十壹章 勇氣和力量 ...
- [ 免費 ] 第三十二章 悲愴好水川 ...
- [ 免費 ] 第三十三章 勝敗能論,只是梟 ...
- [ 免費 ] 第三十四章 壹大群的牛馬駝羊 ...
- [ 免費 ] 第三十五章 戰士和平民,有本 ...
- [ 免費 ] 第三十六章 小結
- [ 免費 ] 第壹章 位高權重
- [ 免費 ] 第二章 叱咤風雲
- [ 免費 ] 第三章 平息國內叛亂
- [ 免費 ] 第四章 紅黑臉待遇
- [ 免費 ] 第五章 狡詐貪婪
- [ 免費 ] 第六章 背叛的跡象
- [ 免費 ] 第七章 傳說
- [ 免費 ] 第八章 得到暗示
- [ 免費 ] 第九章 極度愉悅
- [ 免費 ] 第十章 帝國首相
- [ 免費 ] 第十壹章 經典時刻
- [ 免費 ] 第十二章 開山之作
- [ 免費 ] 第十三章 君子不結黨
- [ 免費 ] 第十四章 高雅純潔
- [ 免費 ] 第十五章 幹掉叛賊
- [ 免費 ] 第十六章 國運分水嶺
- [ 免費 ] 第十七章 威嚴和力量
- [ 免費 ] 第十八章 解燃眉之急
- [ 免費 ] 第十九章 典型的官員
- [ 免費 ] 第二十章 皇帝的特權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燃燒的火鳥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 貝州之賞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 官場瑣事
- [ 免費 ] 第二十四章 開天辟地
- [ 免費 ] 第二十五章 陰性之水
- [ 免費 ] 第二十六章 中國神話
- [ 免費 ] 第二十七章 曝光的事件 ...
- [ 免費 ] 第二十八章 帝國的唯壹繼承人 ...
- [ 免費 ] 第壹章 宋朝病人
- [ 免費 ] 第二章 病情加重
- [ 免費 ] 第三章 強烈回憶
- [ 免費 ] 第四章 太後撤簾
- [ 免費 ] 第五章 公子絕跡
- [ 免費 ] 第六章 公開爭鬥
- [ 免費 ] 第七章 驚天齷齪
- [ 免費 ] 第八章 流雲方寸間
- [ 免費 ] 第九章 法儒不同爐
- [ 免費 ] 第十章 指點江山
- [ 免費 ] 第十壹章 千年疑團說青苗 ...
- [ 免費 ] 第十二章 多面司馬光
- [ 免費 ] 第十三章 士大夫階層
- [ 免費 ] 第十四章 東明縣事件
- [ 免費 ] 第十五章 北宋三人行
- [ 免費 ] 第十六章 冏之王唐坰
- [ 免費 ] 第十七章 異域鐵血鑄輝煌 ...
- [ 免費 ] 第十八章 王安石罷相
- [ 免費 ] 第十九章 人只為己,天誅地滅 ...
- [ 免費 ] 第二十章 遼國分水嶺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習慣性誣陷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 陌上花落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 巔峰悄然退 ...
- [ 免費 ] 第壹章 飛揚的夢
- [ 免費 ] 第二章 俺是兵部的
- [ 免費 ] 第三章 最偉大西征OR最沈痛西 ...
- [ 免費 ] 第四章 真宗朝的秦翰
- [ 免費 ] 第五章 投降
- [ 免費 ] 第六章 扒開黃河
- [ 免費 ] 第七章 必須沖擊三次
- [ 免費 ] 第八章 10萬軍中取主將人頭 ...
- [ 免費 ] 第九章 晝夜不停
- [ 免費 ] 第十章 如此壹生,復有何求 ...
- [ 免費 ] 第十壹章 物資基礎
- [ 免費 ] 第十二章 還有比這更惡毒的言 ...
- [ 免費 ] 第十三章 這是強人手段 ...
- [ 免費 ] 第十四章 聖人PK文豪
- [ 免費 ] 第十五章 毀滅北宋的種子 ...
- [ 免費 ] 第十六章 高滔滔擺烏龍 ...
- [ 免費 ] 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唯有兇殘 ...
- [ 免費 ] 第十八章 西線百年第壹人 ...
- [ 免費 ] 第十九章 熙河軍姚雄
- [ 免費 ] 第二十章 太後英明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同文館之獄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 與弗取,反受其咎 ...
- [ 免費 ] 第壹章 天命
- [ 免費 ] 第二章 宋朝的蘭花
- [ 免費 ] 第三章 北宋終結者
- [ 免費 ] 第四章 黨爭養蠱孰為殃 ...
- [ 免費 ] 第五章 國之少年
- [ 免費 ] 第六章 隱相大人
- [ 免費 ] 第七章 瘋狂的石頭
- [ 免費 ] 第八章 神仙大賣場
- [ 免費 ] 第九章 永遠的西軍
- [ 免費 ] 第十章 公元1111年的盧溝橋事 ...
- [ 免費 ] 第十壹章 完顏
- [ 免費 ] 第十二章 流散的鑌鐵
- [ 免費 ] 第十三章 海上之盟
- [ 免費 ] 第十四章 滅國級蛀蟲
- [ 免費 ] 第十五章 青溪縣的真相 ...
- [ 免費 ] 第十六章 燕雲夢魘
- [ 免費 ] 第十七章 如此復燕雲
- [ 免費 ] 第十八章 歡呼,滅亡
- [ 免費 ] 第十九章 靖康
- [ 免費 ] 第二十章 東京保衛戰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欽宗式沈淪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 烈日驕陽,男兒雄 ...
- [ 免費 ] 第壹章 血色黃昏
- [ 免費 ] 第二章 如果還有明天
- [ 免費 ] 第三章 何至於靖康
- [ 免費 ] 第四章 審判日眾生相
- [ 免費 ] 第五章 趙構集結號
- [ 免費 ] 第六章 皇帝替代品
- [ 免費 ] 第七章 宗澤,過不去的河 ...
- [ 免費 ] 第八章 建炎南渡
- [ 免費 ] 第九章 搜山檢海捉趙構 ...
- [ 免費 ] 第十章 永遠的西軍
- [ 免費 ] 第十壹章 鐵血和尚原
- [ 免費 ] 第十二章 金歸秦檜
- [ 免費 ] 第十三章 西南決戰仙人關 ...
- [ 免費 ] 第十四章 河朔嶽飛
- [ 免費 ] 第十五章 冠絕天下、夢回萬歲 ...
- [ 免費 ] 第十六章 光榮北伐,洛陽城下 ...
- [ 免費 ] 第十七章 淮西軍變
- [ 免費 ] 第十八章 沈默的鎧甲
- [ 免費 ] 第十九章 英雄的黎明
- [ 免費 ] 第壹章 順昌血戰
- [ 免費 ] 第二章 嶽飛第四次北伐 ...
- [ 免費 ] 第三章 踏破賀蘭山缺
- [ 免費 ] 第四章 十年之力,廢於壹旦! ...
- [ 免費 ] 第五章 嶽飛戰場受排擠 ...
- [ 免費 ] 第六章 趙構秦檜耍陰謀收兵權 ...
- [ 免費 ] 第七章 嶽飛之“罪”:莫須有 ...
- [ 免費 ] 第八章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
- [ 免費 ] 第九章 壹把手和二把手的明爭 ...
- [ 免費 ] 第十章 死亡的泥潭
- [ 免費 ] 第十壹章 完顏亮很忙
- [ 免費 ] 第十二章 完顏雍殺死完顏亮 ...
- [ 免費 ] 第十三章 南渡以來僅見的銳氣 ...
- [ 免費 ] 第十四章 雍熙北伐
- [ 免費 ] 第十五章 最傳奇將軍
- [ 免費 ] 第十六章 宿州七日,血流成河 ...
- [ 免費 ] 第十七章 男兒到死心如鐵 ...
- [ 免費 ] 第十八章 亡國之象
- [ 免費 ] 第十九章 成吉思汗登上舞臺 ...
- [ 免費 ] 第二十章 趙構終於死了 ...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十年主角李鳳娘 ...
- [ 免費 ] 第壹章 夢魘江南
- [ 免費 ] 第二章 兩朝內禪
- [ 免費 ] 第三章 韓國戚與趙皇親 ...
- [ 免費 ] 第四章 宰相飛頭去和戎 ...
- [ 免費 ] 第五章 蒙古史詩
- [ 免費 ] 第六章 西北落日
- [ 免費 ] 第七章 壹戰江山野狐嶺 ...
- [ 免費 ] 第八章 天亡此仇
- [ 免費 ] 第九章 西域傳說
- [ 免費 ] 第十章 最愚蠢權臣
- [ 免費 ] 第十壹章 最成功權臣
- [ 免費 ] 第十二章 李全之殤
- [ 免費 ] 第十三章 亡西夏
- [ 免費 ] 第十四章 百年最強了無痕 ...
- [ 免費 ] 第十五章 端平入洛
- [ 免費 ] 第十六章 南方天空最後壹抹晚 ...
- [ 免費 ] 第十七章 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
- [ 免費 ] 第十八章 雲南桃源
- [ 免費 ] 第十九章 上帝折鞭處
- [ 免費 ] 第二十章 暮色襄樊
- [ 免費 ] 第二十壹章 伯顏下江南 ...
- [ 免費 ] 第二十二章 壹片降旗出臨安 ...
- [ 免費 ] 第二十三章 千古悲慟難言處 ...
- [ 免費 ] 第二十四章 崖山之後看中華 ...
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AA+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
简
第二十三章 範仲淹和他的朋友們
2018-9-26 21:22
身在現代,以上的問題都不是問題,我們知道人類在進步,思維無永恒,可在宋朝仁宗景祐三年時,這些問題早就有了終極答案,範仲淹和他的朋友們,也就是他的勢力,絕對堅信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其信心的來源,就在於熟讀的聖賢之書,以及自己優秀的個人品德操守。
我按照對的做了,所以只要妳們與我不同,那麽妳們就是錯的。就這麽簡單。這是不是顯得很無聊,很幼稚,或者很霸道?不,壹點都不,這些就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壹樣,是人類曾經的真理。
並且要強調壹下,如果上面的思維狀態能夠壹直延續下去,而不走樣的話,那麽宋朝就不會有所謂的南宋,北宋就會壹直存在。它之所以滅亡了,就因為連這樣的準則都沒法堅持,後來的爭鬥根本就與對錯無關,只與意氣有關,只與恩怨有關!
好了,回到當時,我們來看壹下範仲淹的勢力都包括了哪些人,以及他們的結合方式。人,基本都很年輕,職務大部分都在館、閣之間,比如,天章閣待制李絨、集賢院校理王質、秘書丞、集賢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館閣校勘歐陽修。
這都是些文學閑職的年輕人,共同的特點是學問好、才學高,他們來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壹起,除了舉國科考制讓他們在同壹個考場追求分數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詩詞文章。比如,歐陽修,他進開封城沒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這個小圈子,與他在文藝復興之都——大宋西京洛陽錢氏沙龍裏的顯赫聲名有關。
於是乎,這些了不起的年輕人們就都聚在了壹起,每日裏行風雅之文,憂天下萬眾之事,日子過得既輕松又神聖,直到他們的帶頭大哥範仲淹與黑惡勢力交上了火。他們再也坐不住了,之後才有呂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薦引朋黨。”
朋黨,這些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啊,妳們知不知道就是這兩個字,往遠裏說,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給毀了;往近裏說,妳們把範仲淹直接廢了。不過這也怪不得他們,因為孔、孟諸賢的聖人語錄裏並沒有“祖宗家法”等內容,他們不該懂的什麽都懂,而該懂的,卻都不屑壹顧。
“祖宗家法”,其中有言者無罪,但更有“異論相攪”。這壹條不懂的話,就永遠沒有辦法明白宋朝的官家們思維最核心的那部分是怎樣運作的。
所以範仲淹和他的朋友們,就壹直郁悶地生存、抗爭、理想、破滅、繼續抗爭……直到滄桑到死。就像他們這時剛開始,就莫名其妙地遭受了第壹次打擊。
無論範仲淹怎樣答辯、追問,呂夷簡的12字箴言威力無窮,皇帝的處罰頒布——剝奪範仲淹京城壹切官職,罷免其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在當年的五月九日,被貶到饒州去做地方官。
……這就是失敗了?我居然失敗了?範仲淹悲憤交集,可是前思後想,卻不允許自己去觸摸最根本的那句話:“該死的,難道說皇帝也瘋了嗎?!”這句話被他緊緊地扼殺在潛意識裏,他所有的力量、信念之來源,都建立在對皇帝的徹底忠誠之上。
皇帝就是神,怎麽會存心捉弄他呢?但事到如今,壹定有錯的人,會是誰?範仲淹苦思冥想,四下張望,他要找出那個關鍵所在,就算是輸了,也要再盡最後壹次力。但他的朋友們比他還要激動,已經先壹步行動了起來。
前面提到的那幾位聲名顯赫的年輕人在皇帝認可的“薦引朋黨”的罪名下主動站了出來,我們就是範仲淹的朋黨,他是個賢人君子,與他為朋,幸也!
看著是很失禮、很違法,甚至可以說很欺君了,但是做得光明正大。因為我們是“行天下之正路”,就是要讓朝裏的奸邪,對,就是首相呂夷簡,要讓他看到,沒有誰能壹手遮天,壓制所有的正義之聲!
多麽的正義啊,那麽多的熱血,壹時之間萬眾矚目,群情激昂,就算沒造反,也把朝中的大佬們嚇出了壹身汗。請註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就在這樣的大場面裏,歐陽修仍然是最為獨特耀眼的壹位大明星,原因就是他的招法實在是太匪夷所思,神妙莫測。就在大家全力以赴修理呂夷簡的時候,他突然間轉身往旁邊沖,抓住了壹個毫不相幹的人,反手就是壹個大嘴巴,讓所有人都記住,這是他的獨門武功,招牌動作!
每當他不爽的時候,禦史臺、知諫院的兄臺們就要小心,他指不定會抓住誰的脖子,來回狠抽大耳光。這回中招就是知諫院的右司諫高若訥。歐陽修寫了封私人信件過去,大罵他身為諫官,尤其就是以前範仲淹的那個位置,居然眼看著呂夷簡這個大奸邪在朝廷裏橫行霸道,卻悶聲不響。試問妳還是個讀書人嗎?
每天還觍著臉出入朝堂,與士大夫為伍,真不知羞恥二字怎麽寫!
高若訥懵了,緊跟著就勃然大怒,要知道高先生也不是好惹的,剛剛結束的倒閻文應事件中,他就是帶頭提起彈劾的人。那是多麽的勇敢,剛過去沒到三個月,正回味無窮呢,突然就變成個膽小鬼、無恥人了?毛頭小子歐陽修,妳才多大,見過多少牛人,辦過多少牛事,居然敢這樣說我?!
但憤怒歸憤怒,高若訥是個知法守法的人。他沒有寫信回罵。嗯,聰明,個人認為他罵不過歐陽修。而是把歐陽大才子的原信上交,請皇帝親自過目。
您看壹下吧,有這麽當官的嗎?您的館閣重地還能留著這樣的人嗎?於是歐陽修的大名脫穎而出,引起了皇帝以及大臣們的特殊關註,大家都想想,他這麽傑出,我們怎樣對待他?
以上種種,雖然熱鬧,但都不是這時的主流。重中之重,仍然在範仲淹的身上,他在鉆牛角尖,他壹定要把事兒弄懂,他不怕死,就怕糊塗,壹定得把這件事是怎麽失敗的整清楚!於是他想來想去,目光集中到壹個人的身上。
沒能扳倒呂夷簡,這個人的幹系也很大,可以說此人是當時宋朝唯壹能對抗呂夷簡的人,無論是資歷、威信、名位還是在皇帝眼中的分量,都只在呂夷簡之上,如果他能及時動手相助,呂夷簡早就卷鋪蓋回家了。但讓人憤怒的是,這人從始至終袖手旁觀,根本無動於衷。
當罪惡出現時,助紂為虐是錯的,漠然視之同時也是錯的,尤其是身有力量可以阻止的人,當作而不做,更是在犯罪!
本著這個原則,範仲淹確定了這個人,並且直接找上門去。他要當面質問,天理公道,朝廷法典,所有的真理都在我壹邊,妳為什麽不幫我?
就是這時,他問出了壹句話。這句話是宋史中至關重要的壹個契機,它是壹代名臣範仲淹苦悶悲憤到了極點,忍無可忍才問出去的。痛心疾首,追問到底,他的臨界點到了。這句話,和對方的回答,就是範仲淹超越歐陽修、韓琦等同輩,甚至遠遠超過王安石、司馬光等人,成為宋朝三百余年間第壹人的根源所在。
偉大的蛻變,終於開始了。
“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王曾王大人,您身為宰相,理所應當弘揚士大夫之中的正氣,可您袖手旁觀,獨善其身,您的盛德,在這方面有重大缺陷!
沒錯,這個能壓制呂夷簡的人就是王曾。以他當年對抗丁謂,制約劉娥的聲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資歷,無論從哪壹點來說,呂夷簡都無法望其項背,如果他適時出手,呂夷簡絕對沒法舉重若輕地勝出。至少王曾說話,他得壹條條地回答,小心謹慎,如履薄冰。
而到了那壹步,範仲淹深信呂夷簡就完蛋了,《百官圖》上都是實據,根本就沒法狡辯!但可惡的是,王曾偏偏躲在壹邊看笑話,從始至終不吭聲。那好吧,我今登門拜訪,請問您到底是為什麽,真的是金口難開?!
這壹次,他如願了,王曾靜靜地凝視他,輕輕地說——“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
又是12個字,範仲淹壹聽,立即就呆住了。從字面上看,完全是答非所問,並沒有回答王曾為什麽要靜觀其敗,無動於衷,可裏面的含義卻非常深邃,就看妳是不是個聰明人,並且是不是個鉆牛角尖的聰明人。
從字面上講,應該這樣翻譯——手握國家權柄的人,如果想讓天下之恩惠皆歸於己,那麽相應的怨恨之情想推給誰?
它的深壹層含義,卻應該這樣解讀——手握國家權柄的人,如果只想讓大家說他的好,不讓大家說他的壞,是可能的嗎?
這是在說,呂夷簡壹定是壞人嗎?他做的都是壞事嗎?試問當家人,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麽都不做的人,才沒人討厭!壹語驚醒夢中人,範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對的嗎?壹些最基本的,平時絕不懷疑的原則觀念在他的心裏升出了問號。
是做聖人,還是做事?是想建設,還是在破壞?回想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確又治水、又救災,做了很多的實事、善事,可是只要壹進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壞之中。比如說,他按著這樣非黑即白的觀念繼續做下去,扳倒了呂夷簡之後還要再做什麽?再去扳倒誰?壹生就只是在打壓、攻擊、謾罵中過日子嗎?
誰做事,就在邊兒上鉚足了勁等著挑錯,這樣的人,就是君子嗎?觀念的改變,帶來思維上的飛越。範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釋什麽,就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壹層的含意。
比如說,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兩相之間的對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證明,只要出現這樣的局面,無論對錯,都是同時下臺的結果。那樣是解恨了,可國家誰去管?民生誰去管?大宋朝堂從上到下,打成壹鍋粥,這就是妳範仲淹的盼望?
宰執之臣,雍容大度,必須從全方位考慮事情,黑、白之外,還有千萬種色彩,要走那條對國家、對朝局最有利的那條路。
所以王曾選擇了沈默,至於說什麽君子、小人、奸邪,見鬼去吧,沒有這些珍稀動物,不分得這樣清,趙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來了,趙光義也活得很快活。
當天範仲淹心神恍惚地離開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壹條道路,可不知該怎麽去走。但走,是壹定的了,他必須離開京城去饒州。臨行前,十裏長亭仍舊有人來送他,那是攜酒而來的王質,他舉杯致意——“範君此行,尤為光耀!”
至此已經是三光了,從“極為”到“愈為”,再到現在的“尤為”,他的品德與意誌逐年疊加,不斷上升,已經成為君子道德人士們的壹面旗幟。可是光陰似箭,範仲淹已經46歲了!壹生至此,老之將至,成就何在?難道就只是壹些虛幻的,於國於民都沒什麽用的聖賢光環嗎?!
範仲淹淒然苦笑,再沒有上兩次的熱血激昂——仲淹至此已經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請準備壹只羊,就當是我的祭品吧。說完上路,把多年以來的追求和京城都拋在腦後,他眼前的路,變得寬廣光明,從今而始,忘身許國,要做實事!
範仲淹走了,在他身後的京城裏還有壹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壹次朋黨幹政風波還沒有收尾。不光是歐陽修等人寧死不屈,發貶到遠邊地區去當官都壹點不在乎,就連京城之外也出了問題。西京洛陽方面的推官蔡襄寫了壹首詩,題名《四賢壹不肖》,四賢就是範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諫院的右司諫高若訥。蔡襄此人文才極高,這首詩迅速從西京波及到東京,又向東京輻射全國,最後竟然連百年好合的友邦遼國也被驚動了。
當時正好有位遼國的使者進京,該仁兄不知出於怎樣的心理,追星族?羨慕宋朝的風氣文化?還是說看出這裏的樂子,回國張揚壹下?他花重金請人抄寫了這首詩,回到幽州之後,就貼到了城門上,讓所有胡漢居民觀看——大宋朝裏好熱鬧,文化太昌盛,連罵架都可以寫成詩!
大宰相呂夷簡的憤怒也終於表露了出來,他授意自己的親信,禦史臺裏的侍禦史韓瀆出面,奏請皇帝在朝堂之上樹立壹張榜,那就是有名的“朋黨榜”,範仲淹的成分變復雜,壹邊是偉大的君子,壹邊是結黨的小人,以他為典型,從此嚴禁結黨營私,組建非法小集團。尤其是強調壹點,絕不允許百官越職言事。
妳們該是幹嘛的,就只能去幹什麽,職務之外,不許亂操心!
至此總結壹下,範仲淹和他的朋友們的奮鬥應該說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讓範仲淹的心靈得到了升華,他的成熟,從壹定意義上來說,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這樣轟轟烈烈的君子整風運動,如果站得稍微高壹些,目光飄過宋朝的邊境,就會發現它們分文不值。異族人已經野心膨脹,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興衰關頭了,還玩這些假招子有什麽用?
虎狼屯於陛下,尚談因果,愚不可及!
李元昊的運氣
西北邊疆劇烈動蕩,吐蕃與黨項兩族浴血廝殺,在爭奪西域真正的霸主地位。戰爭是李元昊挑起的,他敏銳地發現了壹個黃金機會,只要能抓住,他就必將擊潰河湟吐蕃部百萬之眾,壹舉奠定黨項人的千秋偉業。
因為吐蕃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們自從唐末就開始不斷地分裂、動亂、叛變,直到四分五裂之後仍然惡習難改,區區壹個河湟部,在12年之間,就連續發生了兩次政變。
第壹次,發生在公元1023年,即宋天聖元年時,那時擁立唃廝啰當上吐蕃贊普的那個叫李立遵的和尚終於挺不住了,他在三都谷被曹瑋痛打之後,實力大損,但野心仍然不滅,其結果就是被河湟部拋棄,把他扔在了老家宗哥城,全族都遷往邈川,在那裏建立了新的王城。問題不僅沒因此解決,反而加深了。
邈川是另壹個吐蕃強人宰相溫逋奇的老家。這對唃廝啰來說是才脫虎口又進狼群,有名無實的贊普生活還在繼續,危機也在繼續。
危機爆發在公元1035年,即宋朝的景祐二年,溫逋奇突然發動政變,他把唃廝啰少得可憐的班底人員壹網打盡,並且把贊普本人也關進了壹座地牢裏,可以說集突然性、狠毒性於壹體,並且這都發生在他盤踞多年的老根據地裏,應該說天衣無縫,必將成功。
這就是李元昊所發現的黃金機會,國王和宰相的火並,那是千載難逢,要是再不砍過去趁火打劫,他就不是李繼遷的孫子了。他立即派大將蘇奴兒率25000名騎兵晝夜兼程殺進吐蕃,務必要長驅直入,閃電進攻,畢其於壹役,把河湟吐蕃給滅了!
想得很美,可是在頭壹道關口,吐蕃名城貓牛城(今青海西寧東北部,亦名牦牛城)前,蘇奴兒竟然全軍覆沒,連主將本人都沒逃出來!
消息傳來,李元昊又驚又怒,他搞不懂是哪兒出了錯,但是欲望戰勝壹切,他親自出馬,率重兵親征。少年時就曾滅國拓土,他不信這時滅不了壹個動亂中的吐蕃。
可是歷史證明,他真的是什麽都不懂,這也難怪他,根基淺薄是黨項人的通病,暴發戶通常都不理解世家大族的那些古怪又奇妙的老規矩。
說黨項,李繼遷是個被動的反抗者,他面對著暴力和強權,只能依靠暴力和狡詐;看李德明,壹個貌似忠厚,實則兇狠的二世祖,身處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為了生存和利益,他根本從來就沒想過什麽信義和道德;而李元昊是個變本加厲型的升級版李繼遷,從出生到死亡,壹貫唯力是視。
吐蕃就不同,那是壹個有著千年傳承的、獨特歷史信念的古老國度,贊普的意義絕不是中原的皇帝或者黨項的“兀卒”可以比擬。唃廝啰是被關進地牢裏了,可是他被壹個守衛的士兵偷偷放了出來,只身出現在民眾面前,只是壹聲簡單的號召,立即萬眾響應,溫逋奇就此垮臺,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吐蕃之王,贊普!
這樣的事情,就算在最講究君臣之禮,仁義道德的中原都不可能發生。我們所習慣的就是血淋淋的政變,唃斯啰不可能被關進地牢,他會被直接關進棺材!這就是吐蕃的過人之處,幾百年後的政教合壹,早在這時,甚至更加久遠的年代裏,就埋下了深深的種子。
蘇奴兒和25000名騎兵就是這樣覆沒的,他們計算中的動亂根本就沒發生過,相反,吐蕃人在新生的贊普的領導下精神百倍,非常期待廝殺。就這樣,輪到了李元昊在貓牛城下嚎叫,壹個小小的吐蕃外圍邊城,居然讓他堂堂的黨項兀卒禦駕親征,打了壹個多月都沒有動靜!氣死我了―――非得讓我使出祖傳絕招嗎?!
李元昊向貓牛城的吐蕃居民們露出了最真誠的笑容,妳們太偉大了,既堅強又勇敢,還這麽的有信念。我決定和妳們做兄弟,這就撤兵,為了表示敬意和長期的友好願望,臨走前我希望和妳們締結壹個永久的和平條約。
讓我們成為平等互惠的友好臨邦吧,我的手伸出來了,請握住它,讓黨項和吐蕃永遠和平―――!
我按照對的做了,所以只要妳們與我不同,那麽妳們就是錯的。就這麽簡單。這是不是顯得很無聊,很幼稚,或者很霸道?不,壹點都不,這些就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壹樣,是人類曾經的真理。
並且要強調壹下,如果上面的思維狀態能夠壹直延續下去,而不走樣的話,那麽宋朝就不會有所謂的南宋,北宋就會壹直存在。它之所以滅亡了,就因為連這樣的準則都沒法堅持,後來的爭鬥根本就與對錯無關,只與意氣有關,只與恩怨有關!
好了,回到當時,我們來看壹下範仲淹的勢力都包括了哪些人,以及他們的結合方式。人,基本都很年輕,職務大部分都在館、閣之間,比如,天章閣待制李絨、集賢院校理王質、秘書丞、集賢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館閣校勘歐陽修。
這都是些文學閑職的年輕人,共同的特點是學問好、才學高,他們來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壹起,除了舉國科考制讓他們在同壹個考場追求分數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詩詞文章。比如,歐陽修,他進開封城沒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這個小圈子,與他在文藝復興之都——大宋西京洛陽錢氏沙龍裏的顯赫聲名有關。
於是乎,這些了不起的年輕人們就都聚在了壹起,每日裏行風雅之文,憂天下萬眾之事,日子過得既輕松又神聖,直到他們的帶頭大哥範仲淹與黑惡勢力交上了火。他們再也坐不住了,之後才有呂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薦引朋黨。”
朋黨,這些風華正茂的年輕人啊,妳們知不知道就是這兩個字,往遠裏說,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給毀了;往近裏說,妳們把範仲淹直接廢了。不過這也怪不得他們,因為孔、孟諸賢的聖人語錄裏並沒有“祖宗家法”等內容,他們不該懂的什麽都懂,而該懂的,卻都不屑壹顧。
“祖宗家法”,其中有言者無罪,但更有“異論相攪”。這壹條不懂的話,就永遠沒有辦法明白宋朝的官家們思維最核心的那部分是怎樣運作的。
所以範仲淹和他的朋友們,就壹直郁悶地生存、抗爭、理想、破滅、繼續抗爭……直到滄桑到死。就像他們這時剛開始,就莫名其妙地遭受了第壹次打擊。
無論範仲淹怎樣答辯、追問,呂夷簡的12字箴言威力無窮,皇帝的處罰頒布——剝奪範仲淹京城壹切官職,罷免其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在當年的五月九日,被貶到饒州去做地方官。
……這就是失敗了?我居然失敗了?範仲淹悲憤交集,可是前思後想,卻不允許自己去觸摸最根本的那句話:“該死的,難道說皇帝也瘋了嗎?!”這句話被他緊緊地扼殺在潛意識裏,他所有的力量、信念之來源,都建立在對皇帝的徹底忠誠之上。
皇帝就是神,怎麽會存心捉弄他呢?但事到如今,壹定有錯的人,會是誰?範仲淹苦思冥想,四下張望,他要找出那個關鍵所在,就算是輸了,也要再盡最後壹次力。但他的朋友們比他還要激動,已經先壹步行動了起來。
前面提到的那幾位聲名顯赫的年輕人在皇帝認可的“薦引朋黨”的罪名下主動站了出來,我們就是範仲淹的朋黨,他是個賢人君子,與他為朋,幸也!
看著是很失禮、很違法,甚至可以說很欺君了,但是做得光明正大。因為我們是“行天下之正路”,就是要讓朝裏的奸邪,對,就是首相呂夷簡,要讓他看到,沒有誰能壹手遮天,壓制所有的正義之聲!
多麽的正義啊,那麽多的熱血,壹時之間萬眾矚目,群情激昂,就算沒造反,也把朝中的大佬們嚇出了壹身汗。請註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就在這樣的大場面裏,歐陽修仍然是最為獨特耀眼的壹位大明星,原因就是他的招法實在是太匪夷所思,神妙莫測。就在大家全力以赴修理呂夷簡的時候,他突然間轉身往旁邊沖,抓住了壹個毫不相幹的人,反手就是壹個大嘴巴,讓所有人都記住,這是他的獨門武功,招牌動作!
每當他不爽的時候,禦史臺、知諫院的兄臺們就要小心,他指不定會抓住誰的脖子,來回狠抽大耳光。這回中招就是知諫院的右司諫高若訥。歐陽修寫了封私人信件過去,大罵他身為諫官,尤其就是以前範仲淹的那個位置,居然眼看著呂夷簡這個大奸邪在朝廷裏橫行霸道,卻悶聲不響。試問妳還是個讀書人嗎?
每天還觍著臉出入朝堂,與士大夫為伍,真不知羞恥二字怎麽寫!
高若訥懵了,緊跟著就勃然大怒,要知道高先生也不是好惹的,剛剛結束的倒閻文應事件中,他就是帶頭提起彈劾的人。那是多麽的勇敢,剛過去沒到三個月,正回味無窮呢,突然就變成個膽小鬼、無恥人了?毛頭小子歐陽修,妳才多大,見過多少牛人,辦過多少牛事,居然敢這樣說我?!
但憤怒歸憤怒,高若訥是個知法守法的人。他沒有寫信回罵。嗯,聰明,個人認為他罵不過歐陽修。而是把歐陽大才子的原信上交,請皇帝親自過目。
您看壹下吧,有這麽當官的嗎?您的館閣重地還能留著這樣的人嗎?於是歐陽修的大名脫穎而出,引起了皇帝以及大臣們的特殊關註,大家都想想,他這麽傑出,我們怎樣對待他?
以上種種,雖然熱鬧,但都不是這時的主流。重中之重,仍然在範仲淹的身上,他在鉆牛角尖,他壹定要把事兒弄懂,他不怕死,就怕糊塗,壹定得把這件事是怎麽失敗的整清楚!於是他想來想去,目光集中到壹個人的身上。
沒能扳倒呂夷簡,這個人的幹系也很大,可以說此人是當時宋朝唯壹能對抗呂夷簡的人,無論是資歷、威信、名位還是在皇帝眼中的分量,都只在呂夷簡之上,如果他能及時動手相助,呂夷簡早就卷鋪蓋回家了。但讓人憤怒的是,這人從始至終袖手旁觀,根本無動於衷。
當罪惡出現時,助紂為虐是錯的,漠然視之同時也是錯的,尤其是身有力量可以阻止的人,當作而不做,更是在犯罪!
本著這個原則,範仲淹確定了這個人,並且直接找上門去。他要當面質問,天理公道,朝廷法典,所有的真理都在我壹邊,妳為什麽不幫我?
就是這時,他問出了壹句話。這句話是宋史中至關重要的壹個契機,它是壹代名臣範仲淹苦悶悲憤到了極點,忍無可忍才問出去的。痛心疾首,追問到底,他的臨界點到了。這句話,和對方的回答,就是範仲淹超越歐陽修、韓琦等同輩,甚至遠遠超過王安石、司馬光等人,成為宋朝三百余年間第壹人的根源所在。
偉大的蛻變,終於開始了。
“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王曾王大人,您身為宰相,理所應當弘揚士大夫之中的正氣,可您袖手旁觀,獨善其身,您的盛德,在這方面有重大缺陷!
沒錯,這個能壓制呂夷簡的人就是王曾。以他當年對抗丁謂,制約劉娥的聲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資歷,無論從哪壹點來說,呂夷簡都無法望其項背,如果他適時出手,呂夷簡絕對沒法舉重若輕地勝出。至少王曾說話,他得壹條條地回答,小心謹慎,如履薄冰。
而到了那壹步,範仲淹深信呂夷簡就完蛋了,《百官圖》上都是實據,根本就沒法狡辯!但可惡的是,王曾偏偏躲在壹邊看笑話,從始至終不吭聲。那好吧,我今登門拜訪,請問您到底是為什麽,真的是金口難開?!
這壹次,他如願了,王曾靜靜地凝視他,輕輕地說——“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
又是12個字,範仲淹壹聽,立即就呆住了。從字面上看,完全是答非所問,並沒有回答王曾為什麽要靜觀其敗,無動於衷,可裏面的含義卻非常深邃,就看妳是不是個聰明人,並且是不是個鉆牛角尖的聰明人。
從字面上講,應該這樣翻譯——手握國家權柄的人,如果想讓天下之恩惠皆歸於己,那麽相應的怨恨之情想推給誰?
它的深壹層含義,卻應該這樣解讀——手握國家權柄的人,如果只想讓大家說他的好,不讓大家說他的壞,是可能的嗎?
這是在說,呂夷簡壹定是壞人嗎?他做的都是壞事嗎?試問當家人,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麽都不做的人,才沒人討厭!壹語驚醒夢中人,範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對的嗎?壹些最基本的,平時絕不懷疑的原則觀念在他的心裏升出了問號。
是做聖人,還是做事?是想建設,還是在破壞?回想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確又治水、又救災,做了很多的實事、善事,可是只要壹進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壞之中。比如說,他按著這樣非黑即白的觀念繼續做下去,扳倒了呂夷簡之後還要再做什麽?再去扳倒誰?壹生就只是在打壓、攻擊、謾罵中過日子嗎?
誰做事,就在邊兒上鉚足了勁等著挑錯,這樣的人,就是君子嗎?觀念的改變,帶來思維上的飛越。範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釋什麽,就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壹層的含意。
比如說,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兩相之間的對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證明,只要出現這樣的局面,無論對錯,都是同時下臺的結果。那樣是解恨了,可國家誰去管?民生誰去管?大宋朝堂從上到下,打成壹鍋粥,這就是妳範仲淹的盼望?
宰執之臣,雍容大度,必須從全方位考慮事情,黑、白之外,還有千萬種色彩,要走那條對國家、對朝局最有利的那條路。
所以王曾選擇了沈默,至於說什麽君子、小人、奸邪,見鬼去吧,沒有這些珍稀動物,不分得這樣清,趙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來了,趙光義也活得很快活。
當天範仲淹心神恍惚地離開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壹條道路,可不知該怎麽去走。但走,是壹定的了,他必須離開京城去饒州。臨行前,十裏長亭仍舊有人來送他,那是攜酒而來的王質,他舉杯致意——“範君此行,尤為光耀!”
至此已經是三光了,從“極為”到“愈為”,再到現在的“尤為”,他的品德與意誌逐年疊加,不斷上升,已經成為君子道德人士們的壹面旗幟。可是光陰似箭,範仲淹已經46歲了!壹生至此,老之將至,成就何在?難道就只是壹些虛幻的,於國於民都沒什麽用的聖賢光環嗎?!
範仲淹淒然苦笑,再沒有上兩次的熱血激昂——仲淹至此已經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請準備壹只羊,就當是我的祭品吧。說完上路,把多年以來的追求和京城都拋在腦後,他眼前的路,變得寬廣光明,從今而始,忘身許國,要做實事!
範仲淹走了,在他身後的京城裏還有壹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壹次朋黨幹政風波還沒有收尾。不光是歐陽修等人寧死不屈,發貶到遠邊地區去當官都壹點不在乎,就連京城之外也出了問題。西京洛陽方面的推官蔡襄寫了壹首詩,題名《四賢壹不肖》,四賢就是範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諫院的右司諫高若訥。蔡襄此人文才極高,這首詩迅速從西京波及到東京,又向東京輻射全國,最後竟然連百年好合的友邦遼國也被驚動了。
當時正好有位遼國的使者進京,該仁兄不知出於怎樣的心理,追星族?羨慕宋朝的風氣文化?還是說看出這裏的樂子,回國張揚壹下?他花重金請人抄寫了這首詩,回到幽州之後,就貼到了城門上,讓所有胡漢居民觀看——大宋朝裏好熱鬧,文化太昌盛,連罵架都可以寫成詩!
大宰相呂夷簡的憤怒也終於表露了出來,他授意自己的親信,禦史臺裏的侍禦史韓瀆出面,奏請皇帝在朝堂之上樹立壹張榜,那就是有名的“朋黨榜”,範仲淹的成分變復雜,壹邊是偉大的君子,壹邊是結黨的小人,以他為典型,從此嚴禁結黨營私,組建非法小集團。尤其是強調壹點,絕不允許百官越職言事。
妳們該是幹嘛的,就只能去幹什麽,職務之外,不許亂操心!
至此總結壹下,範仲淹和他的朋友們的奮鬥應該說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讓範仲淹的心靈得到了升華,他的成熟,從壹定意義上來說,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這樣轟轟烈烈的君子整風運動,如果站得稍微高壹些,目光飄過宋朝的邊境,就會發現它們分文不值。異族人已經野心膨脹,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興衰關頭了,還玩這些假招子有什麽用?
虎狼屯於陛下,尚談因果,愚不可及!
李元昊的運氣
西北邊疆劇烈動蕩,吐蕃與黨項兩族浴血廝殺,在爭奪西域真正的霸主地位。戰爭是李元昊挑起的,他敏銳地發現了壹個黃金機會,只要能抓住,他就必將擊潰河湟吐蕃部百萬之眾,壹舉奠定黨項人的千秋偉業。
因為吐蕃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們自從唐末就開始不斷地分裂、動亂、叛變,直到四分五裂之後仍然惡習難改,區區壹個河湟部,在12年之間,就連續發生了兩次政變。
第壹次,發生在公元1023年,即宋天聖元年時,那時擁立唃廝啰當上吐蕃贊普的那個叫李立遵的和尚終於挺不住了,他在三都谷被曹瑋痛打之後,實力大損,但野心仍然不滅,其結果就是被河湟部拋棄,把他扔在了老家宗哥城,全族都遷往邈川,在那裏建立了新的王城。問題不僅沒因此解決,反而加深了。
邈川是另壹個吐蕃強人宰相溫逋奇的老家。這對唃廝啰來說是才脫虎口又進狼群,有名無實的贊普生活還在繼續,危機也在繼續。
危機爆發在公元1035年,即宋朝的景祐二年,溫逋奇突然發動政變,他把唃廝啰少得可憐的班底人員壹網打盡,並且把贊普本人也關進了壹座地牢裏,可以說集突然性、狠毒性於壹體,並且這都發生在他盤踞多年的老根據地裏,應該說天衣無縫,必將成功。
這就是李元昊所發現的黃金機會,國王和宰相的火並,那是千載難逢,要是再不砍過去趁火打劫,他就不是李繼遷的孫子了。他立即派大將蘇奴兒率25000名騎兵晝夜兼程殺進吐蕃,務必要長驅直入,閃電進攻,畢其於壹役,把河湟吐蕃給滅了!
想得很美,可是在頭壹道關口,吐蕃名城貓牛城(今青海西寧東北部,亦名牦牛城)前,蘇奴兒竟然全軍覆沒,連主將本人都沒逃出來!
消息傳來,李元昊又驚又怒,他搞不懂是哪兒出了錯,但是欲望戰勝壹切,他親自出馬,率重兵親征。少年時就曾滅國拓土,他不信這時滅不了壹個動亂中的吐蕃。
可是歷史證明,他真的是什麽都不懂,這也難怪他,根基淺薄是黨項人的通病,暴發戶通常都不理解世家大族的那些古怪又奇妙的老規矩。
說黨項,李繼遷是個被動的反抗者,他面對著暴力和強權,只能依靠暴力和狡詐;看李德明,壹個貌似忠厚,實則兇狠的二世祖,身處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為了生存和利益,他根本從來就沒想過什麽信義和道德;而李元昊是個變本加厲型的升級版李繼遷,從出生到死亡,壹貫唯力是視。
吐蕃就不同,那是壹個有著千年傳承的、獨特歷史信念的古老國度,贊普的意義絕不是中原的皇帝或者黨項的“兀卒”可以比擬。唃廝啰是被關進地牢裏了,可是他被壹個守衛的士兵偷偷放了出來,只身出現在民眾面前,只是壹聲簡單的號召,立即萬眾響應,溫逋奇就此垮臺,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吐蕃之王,贊普!
這樣的事情,就算在最講究君臣之禮,仁義道德的中原都不可能發生。我們所習慣的就是血淋淋的政變,唃斯啰不可能被關進地牢,他會被直接關進棺材!這就是吐蕃的過人之處,幾百年後的政教合壹,早在這時,甚至更加久遠的年代裏,就埋下了深深的種子。
蘇奴兒和25000名騎兵就是這樣覆沒的,他們計算中的動亂根本就沒發生過,相反,吐蕃人在新生的贊普的領導下精神百倍,非常期待廝殺。就這樣,輪到了李元昊在貓牛城下嚎叫,壹個小小的吐蕃外圍邊城,居然讓他堂堂的黨項兀卒禦駕親征,打了壹個多月都沒有動靜!氣死我了―――非得讓我使出祖傳絕招嗎?!
李元昊向貓牛城的吐蕃居民們露出了最真誠的笑容,妳們太偉大了,既堅強又勇敢,還這麽的有信念。我決定和妳們做兄弟,這就撤兵,為了表示敬意和長期的友好願望,臨走前我希望和妳們締結壹個永久的和平條約。
讓我們成為平等互惠的友好臨邦吧,我的手伸出來了,請握住它,讓黨項和吐蕃永遠和平―――!